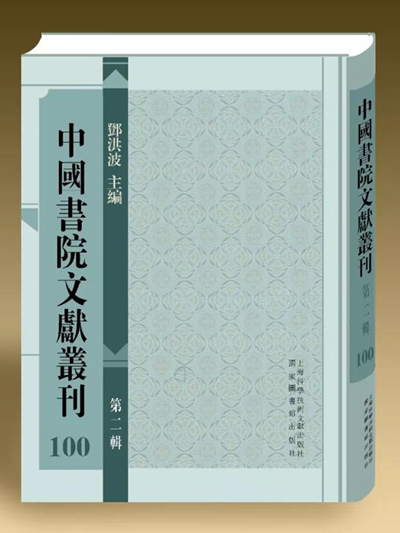
書院,是儒家文化特有的一種文化與教育現象。從唐代出現的雛形開始,它在長達千餘年的中國歷史中扮演著非常獨特和重要的角色。
它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幹與核心——儒學及其研究者、傳播者——儒家的道場。書院是儒家的首創,在其發展過程中,成爲儒學寄生與發展的重要載體和平臺。所以,它的命運始終與儒學和儒家的命運緊密相連,儒學興則書院盛,儒學衰則書院敗。清末民初,廢科舉、辦新學,書院也就走進了它的低谷。但是,歷史總是愛和人類開玩笑,没有人會想到,進入了二十一世紀以後,書院竟然又煥發新生了。在新時代,它的勃興居然如雨後春笋般“瘋狂”與勢不可擋。
書院從它誕生的那一天起就有官方和民間的雙重性質,它既借助於體制的資源和模式,又有游離於體制之外的自由講學和辦學的精神,它一直被視爲官方主流教育體制的一個補充、補缺。所謂“補充”,是説它彌補了體制內教育資源的不足,官學無法覆蓋的,書院彌補了。所謂“補缺”,是説它補了體制內教育以應試(應科舉)爲目的之缺:書院教育以成人、成賢爲目的,以傳道(儒家的道統)爲核心。實際上,從明代中後期以來,官學越來越流於形式,書院却以“補充”“補缺”之身而真正承擔起國民教育的責任。放眼人類教育史,古今中外,中國的書院,恐怕是一種絶無僅有的與功利不搭或少搭的教育形態。而且這種與功利保持距離的教育形態在中國的民間一直很好地被呵護并發展著。書院的辦學資金部分來源於官方的籌集,部分來源於民間的捐助,官員、商人、士紳是這種捐助的主體。中國的書院綿延千年之久,民間捐助者的貢獻居功至偉,官方的支持也是至關重要的。
正因爲書院一定程度游離於體制之外,正因爲它與功利保持距離,所以,能看到體制的弊端,能不受羈絆地思考與研究。於是,中國的書院成了生産新思想、新學術、新理論的工廠。而這些新思想、新學術、新理論又對社會、人心發生了反哺,從而影響了國家與社會的發展。
朱子是第一位從理論與實踐兩個層面上對中國書院的制度建設,理論建構,辦學目標、方針、方法等做出重大貢獻的學者。他的《白鹿洞書院學規》是一篇劃時代的綱領性文件,爲中國書院的建設與發展打下了基石。直到今天,這篇文獻依然是新時代書院實踐的“源頭活水”。而他在嶽麓書院的一系列教育實踐,則爲後人留下了健康與科學的教學與科研生態的典範。中國的書院之所以有著那麽强勁的生命力和生機活潑的內生動能,不能不説與朱子有關。
中國書院在千餘年的發展中,爲記録其歷史、教學、經濟、學術、考課等,留下了數以萬計的各種文獻,包括書院記、書院志、學規、章程、課藝、講義、會録、同門譜、藏書目録、刻書目録、山長志、學田志、日記等。這些文獻不僅對研究書院至關重要,對研究中國的歷史、文化、學術、政治等都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意義。遺憾的是,隨著書院的没落,這些文獻也隨之散佚。國力的强盛與傳統文化的復興,終於使書院文獻獲得了一個新生的機會。以鄧洪波教授領銜的課題組發起對中國書院文獻的整理,實在是一件對民族文化功德無量的好事。我參加了本課題的可行性論證,拜讀了全部課題報告以後我意識到,這是一次全面的、系統的整理,課題完成,也就意味著完成了中國書院文獻的集大成。這是一件值得所有關注書院的學者高興和期待的學術盛事。
當然,講到這件盛事就不能不講到鄧洪波教授。鄧洪波并不是最早關注和研究中國書院的學者,但他却是一位始終不渝地專注於這個領域而默默耕耘的學者。他的可貴之處在於,當書院還處於一個被人遺忘和被絶大多數人冷落的年代,他始終没有放棄。他以一己之力,搜羅鈎沉,爬梳剔抉,考鏡源流,排比論列,終成一家之説。現在書院研究成了“顯學”,洪波并不被“顯”而空疏、好高求遠的世俗所裹挾,而是踏踏實實地做了大量的文獻整理與研究工作,他的抱負和執著不能不令人感佩。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書院文獻整理與研究”的成果就要出版了,它包括書目、影印、點校、研究幾個系列,這是一件盛事。洪波兄要我寫一個序,但是我對書院没有研究,真是不知道這個序該從何説起,衹好談談自己對書院的一些基本認識,以塞文責,也算是不負洪波兄的一片美意。
朱傑人
華東師範大學終身教授
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榮譽會長
中華朱子學會常務副會長
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二日於海上桑榆匪晚齋
圖文編發:中國文化書院(陽明文化研究院) 中華傳統文化與貴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 辦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