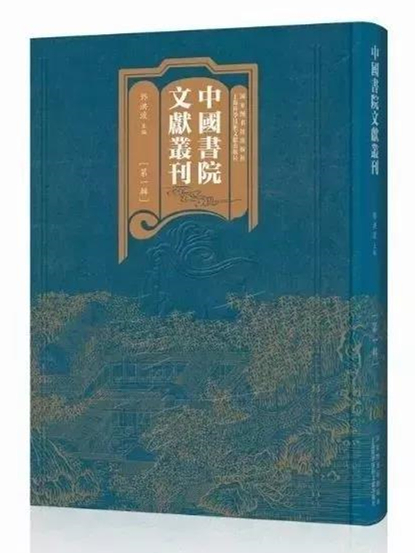
書院是中國古代教育史上影響最大的教育文化機構。鄧洪波教授認爲書院是獨特的文化教育組織。所謂獨特,我以爲大概是因爲它既非官學,亦非純粹的私學,但又與官府、官員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一直得到各級官府的支持和資助。例如朱熹修復白鹿洞書院、嶽麓書院,阮元創詁經精舍、學海堂,張之洞建尊經書院、廣雅書院,都是任官期間的事。許多官員也將創建書院、講研義理學問視爲一種可以自豪的政績,希望以書院長育人才、開啓民智、移風易俗。比如湯顯祖貶徐聞典史時創立貴生書院,親往講學。他任遂昌知縣時,建相圃書院,撥寺廟道觀部分食田歸書院收租,以作修葺房屋之費及諸生膏火之助。他自己亦在書院中“與諸生講德問字”“陳説天性大義”而不疲。但書院又非官學,書院的科目設置、講論內容都由著名學者擔任的書院山長、主講設定與主持,官府干涉有限。書院與官學既相區别又有聯繫,故清末廢科舉,改書院爲學堂,使中國教育由古代邁入現代,便能自然銜接而水到渠成了。
書院與私學的關係也十分密切。春秋以降,學在王官漸變爲學在四夷,私人講學之風漸盛。孔子的講學活動,既有與弟子講論六藝、切磋琢磨的謹嚴與認真,亦有“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的散淡與閑適,與書院自由講學的精神一脉相通。兩漢經師講學,受業者不遠千里而至,講讀之所則“講堂”“精舍”隨意立名。馬融“教養諸生常有千數”,設絳紗帳講學,“前授生徒,後列女樂”,是最氣派的一家。魏晉南北朝戰亂頻仍,但講學之風不息。上述講學活動和組織形式,對後來書院的出現有著深刻影響。
書院之名始於唐代。東西二都設立的麗正書院和集賢殿書院,有著國家藏書、校書、修書及由此而辨章學術的深厚傳統,它標志著書院之名得到官方認可和提倡。其實,最先出現的還是民間書院,有唐代文獻與地方史志爲證。《全唐詩》中也提到過十三所作爲士大夫私人讀書治學之所的書院。也就是説,書院源出於唐代私人治學的書齋和官府整理典籍的衙門,是官、民兩股力量相互作用的結果。
唐五代之際,開始出現聚徒講學性質的書院,江西的桂巖、東佳與燕山竇氏皆是其佼佼者。書院的大繁榮則要進入到宋代,著名的“濂、洛、關、閩”四家,既是學派,也是講學團體,且師生傳承,歷久不衰。他們中的許多人都參與過書院的創建和講學活動,通德鴻儒,發幽闡微,風雅相續,輝映壇席。元代書院數百所,明清書院各數千所,是書院的鼎盛時期。
書院講求敦勵品節、探研經義,以求知行合一,長育人才。主持者往往以自身風範言傳身教,并不刻意傳授系統知識。尤其是宋代書院批判地繼承了兩漢的講經之風,注重闡釋以四書爲中心的儒家經典義理,理學借書院講學得以光大。此後,隨著時代的需要和地方學術風氣的浸潤,書院講學內容各有側重,或義理,或實學,或訓詁,或辭章,而書院的教學方式也不拘一格,講論、問答、辯説、切磋,形式多樣,效果顯著,頗有百花齊放之勢。當然,書院的根本任務是養育人才,故與唐宋元明清各代科舉密切相關,講論經義、草擬試策、熟記帖括、習練論説,自然也是書院學習的重要內容。一些著名學者掌教書院,往往能形成學派,光大學術,引領學風。不同學派學者在書院的論辯駁難,也使書院成爲交流學術、推廣宣傳學派主張的方便場所。書院促進了學術的發展,僅以清代爲例,著名學者如黄宗羲、湯斌、張伯行、杭世駿、齊召南、全祖望、姚鼐、盧文弨、王鳴盛、程瑶田、錢大昕、章學誠、洪亮吉、孫星衍、阮元、陳壽祺、顧廣圻、陳澧、劉熙載、俞樾、張之洞、王先謙、繆荃孫、皮錫瑞等,這些在清代學術史上閃耀的群星,無一不在書院任過山長或主講,將他們在書院講學的學術貢獻稍作整理,便能勾勒出清代學術史的梗概。可以説唐宋以來中國古代教育、文化、學術的發展實有賴於書院的繁榮,程朱理學、陸王心學、乾嘉漢學、晚清新學的産生與興盛,都與書院密切相關。書院以及鄉村的義塾、義學,使中國儒學傳承的血脉貫通而達至社會底層,從而也使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有了最堅實的社會基礎,中國文化綿延不絶,書院有其莫大貢獻。
書院作爲中國古代獨特的文化教育組織,深深影響著唐宋以來教育、文化、學術的發展,近百年來學者往往將古代書院與現代學校比照考察,研究書院的論著日積月纍,頗爲可觀。特别是近十數年來,書院研究更有日漸興盛之勢。許多研究已涉及書院的各個方面,如書院制度及其組織形式,書院的課程設置、講會制度和開講儀式,書院的學規章程和管理模式,書院的經濟活動和經費開支,書院的藏書與刻書活動等,涉及面雖廣,但研究似乎尚不夠深入全面。究其原因,自然與目前學術界所見書院文獻資料不豐富有關。例如,僅清代書院即有五千餘所,而迄今許多論著所涉書院僅百餘所,眼界和格局便受局限。大量書院文獻散藏各處,許多文獻甚至不爲人知,或少人問津,研究自然不夠全面,也難以深入。材料的缺失嚴重阻滯了書院研究的進程,因此,比較齊全地搜輯目前存世的書院文獻,分門别類地加以影印或點校出版,對於書院研究而言,事莫大於此,更莫急於此。現在鄧洪波教授主持的“中國書院文獻整理與研究”工程即將出版幾種專題叢書,使此大事、急事終獲成功,必將爲中國書院研究的繁盛帶來新局面。
鄧洪波教授及其團隊的成果,對於書院研究及與書院相關的研究,至少有三大貢獻:
其一,爲書院研究提供了相當完備的資料。他們編纂了比較完善的書院文獻總目及總目提要,第一次揭示了現存書院文獻的全貌,在此基礎上又將現存近一千五百種書院文獻中的一千餘種影印出版,成《中國書院文獻叢刊》,進而又擇其中尤爲重要者約一百五十種點校出版,成《中國書院文獻薈要》。學者研究實踐證明,書院研究賴以深入和發展的基礎是書院文獻的全面搜求與系統整理,鄧洪波教授的團隊完成了這項工作。他們的書院總目及有選擇地影印、點校的占總量七成的書院文獻,不僅爲研究者提供了方便,也爲一般讀者瞭解中國書院指出了門徑。大量過去未被發掘、利用,而又相對完備、系統的資料,經他們網羅放失,搜剔叢殘,使遺編剩稿,顯晦并出,吉光片羽,終免湮没,而流風餘韻亦可相因而不墜。相信今後的書院研究一定會有許多新發現、新視角和新課題,也必將産生許多更近於史實的新結論。
其二,整理與研究高度融合,産生了系列成果。他們的工作使書目、《中國書院文獻叢刊》《中國書院文獻薈要》、研究論著等互相呼應,是將整理和研究結合得比較好的範例,也爲古籍整理與研究工作如何互相促進提供了經驗。《書院文獻總目》揭示藏館和版本,大大提高了書目的品質和使用價值,《書院文獻總目提要》本身便是研究成果,它不僅指引門徑,也爲進一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提供了基礎和方便。而《中國書院志史》及其他研究論集,既是書院研究的新收穫,也是書院研究深化的表現。他們的整理研究系列成果,不僅大大促進了書院研究自身的深入和發展,還旁涉中國古代政治史、經濟史、教育史、思想史、文化史、文學史等各領域,從而也必將有利於上述領域的綜合研究别開生面,以至進一步推進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和發展。
其三,是大型專題資料叢書的新收穫。大型專題性資料叢書對於相關專題學術研究的作用是無與倫比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學術界一直有編纂大型專題資料叢書的傳統,上世紀五十年代,中國史學會主持編纂了《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包括《鴉片戰争》《太平天國》《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義和團》《辛亥革命》等十餘種專題資料叢書。這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成爲研究中國近代史的中外學者必讀資料,也成就了一批國內外的教授、博士,産生過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其後,一些出版機構如中華書局、上海古籍出版社、國家圖書館出版社、鳳凰出版社等也組織或出版過許多大型專題資料叢書,一些專題檔案也陸續刊布。專題資料叢書提供的材料比較全面、系統,使用方便,學者在比較研究中更易發現問題、解决問題,也可以避免盲人摸象、以偏概全的弊端,故頗受學者歡迎。鄧洪波教授主持的書院文獻整理研究工作産生的幾種大型資料叢書,是近年來專題資料叢書的新收穫,也必將會爲中國書院研究做出巨大貢獻。
鄧洪波教授是較早注意整理書院文獻、研究中國書院的學者之一,也是當代中國書院研究的名家。數十年的潛心研究和執著追求,使他的研究成果得到學術界的高度重視,有很好的影響。現在他又主持完成了這樣一件嘉惠學林的大工程,實在令人感動和欽佩,故不避淺陋而爲之序,以表達對鄧洪波教授及其團隊學者的敬意。
楊忠
教育部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秘書長
北京大學教授
二〇一八年七月三十日於北京大學藍旗營
圖文編發:中國文化書院(陽明文化研究院) 中華傳統文化與貴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 辦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