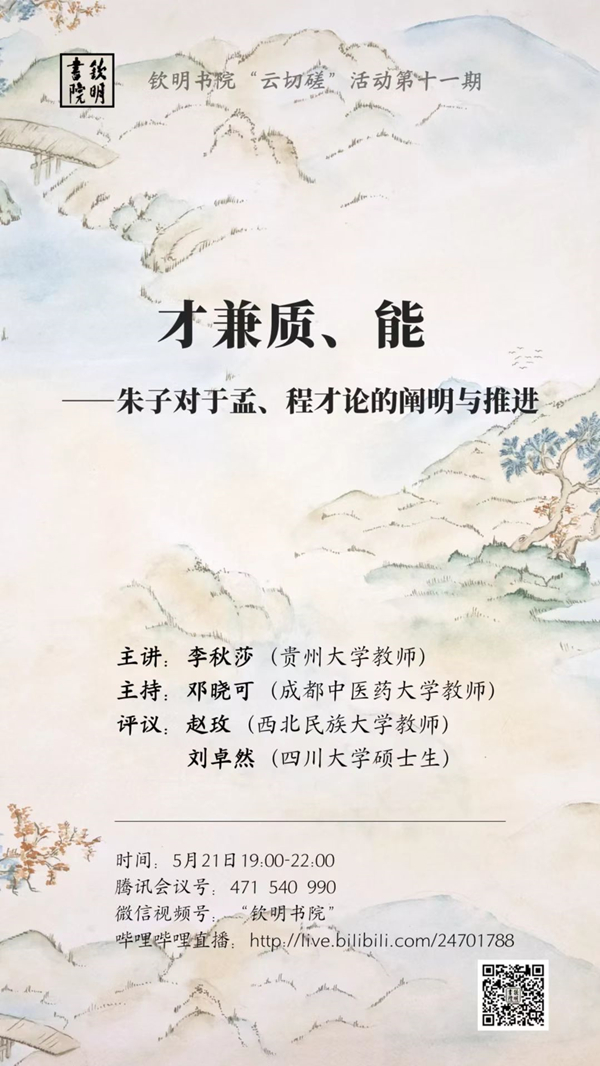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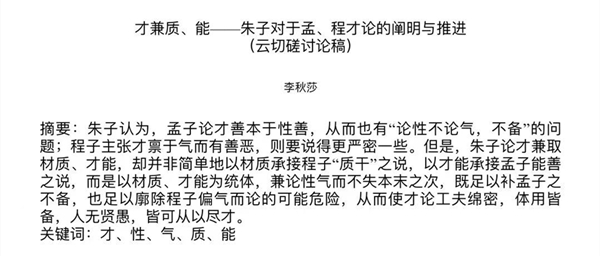
5月21日晚七点到十点,钦明书院第十一期“云切磋”活动在腾讯会议平台举行。活动主题为“才兼质、能——朱子对于孟、程才论的阐明与推进”,由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李秋莎老师任主讲,成都中医药大学邓晓可老师任主持,西北民族大学赵玫老师、四川大学刘卓然同学任评议。
李秋莎提出:“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性不论气,不明;二之,则不是”是程伊川对北宋及以前人性论的重要论断,朱子对此十分称赏,且认为孟子在讨论“才”的时候,“不备”问题同样存在。即:孟子也只讨论了出于善性的善才,而未讨论气禀差异所导致的才质、才能区别。且朱子同样指出,“才只一般”,若认为有出于性和出于气的两种才,也必然导致二本而“不是”。那么,我们可以将认为“性出于天,才禀于气”,气有清浊则才有善恶的程伊川对应于“论气不论性”之“不明”吗?且不说程伊川并不否认孟子语境下的才善,若将强调善性必然着落于气禀直接视作对于性的忽略,无疑是危险的。
孟子强调性不可见,发而为情,既然四端人所皆有,不容违遏殆尽,足徵四德人所固有,那么,人在能善上的差异即使悬若霄壤,也只是尽才不尽才所致。倘若人尽其才,所有人必定能其性中所有之善。此由性为生性所自涵,并无可能性上的差异。无论气禀昏明强弱是否致使力有大小,对于单个的人来说,在“总是能用完自己的十分去做”这个意义上,才总是足够的。此由人禀正通之气,必能通蔽开塞保证,与具体气禀无关。故此,孟子认为上天降才,在能善上并无区别;人之尽才,其可能也受生而然。
如说孟子论“天之降才”近才质,“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近才能,才质、才能皆善,则程伊川论才明显要更强调才质。他以质干、材植来解释才,认为既然气禀必然万殊,那么人的才质也就必然有美恶的区别。才的美恶决定了用的不同,就像曲木可以造车轮,直木可以造梁栋。就此,程伊川认同人将本来可以造车轮、梁栋的才质凿坏了,确实非才之罪,但这并不掩去才质有曲直的区别。才质美恶相差甚远,致使上智下愚并不能完全说“非才之罪”——人的才质甚至会浊恶到把为善的可能紧紧拴缚,腾挪不得。面对因才质浊恶而为善特别困难的人,我们并不合适仅责备他们不肯尽才,而需正视才对人为善迟速难易的影响。也因此,不同于孟子认为尽才只需扩充善端,程子认为努力尽才所致的气质变化,只是长久用力之后的知善、行善之进(“虽愚必明,虽柔必强”),不应把精力花在只能勉强改善的艺能上(“钝者不可使利”)。
朱子释才,说:“才犹材质,人之能也。”看似兼取孟、程,但并非孟、程才论的简单相加。才质也需兼论性气,才能也需兼论性气。性出于天,气也出于天,只是有纯、驳之别。气质之性既是天命之性在气质中,并无二性,本善的才质就必定落实于聪明果敢正直中和。人的为善既是要即事即物一一止于至善,为善的才能也就必定落实于视明听聪貌恭言从思睿。才质才能一体一用,性在气中,方能从根本上避免“不备”、“不明”、“不是”的风险,指引人不因美恶才质局限其能善,不因大小才能局限其本善,从而真正尽才。
李秋莎主讲完毕,赵玫、刘卓然分别作了评议,四川大学高小强老师、曾海军老师及部分与会同学分别提问。问题集中于:“才有美恶”与“才有善恶”有什么区别?怎样理解程伊川的才论?德与才有何关系?才质、才能会相互拘限吗?怎样变化气质?怎样尽才?活动参与师生进行了深入讨论。
图文:中国文化书院 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 李秋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