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场一央 文
胡嘉明、潘承健[1]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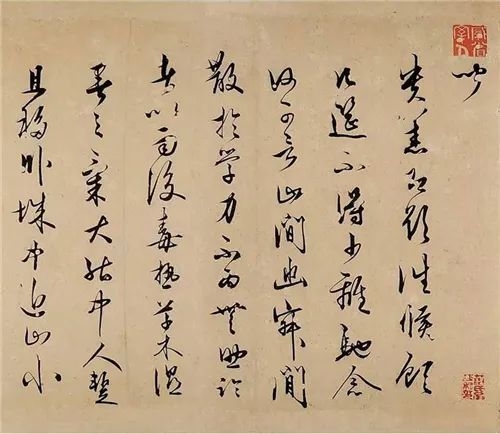
作者简介
大場一央(oubakazuo/オオバカズオ),1979年生,早稻田大学文学博士,现任教于早稻田大学。博士论文做王阳明(「心即理-王陽明前期思想の研究」),发表论文:「王陽明の『立志』について」(《日本中国学会報》第58集・2006年)、「王陽明の思想形成における龍場大悟の位置」(《早稲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紀要》第52輯・第1分冊・2007年)、「王陽明前期思想における『誠』について」(《論叢・アジアの文化と思想》第17号・2008年)等。2003年早稻田大学成立“阳明书院”,该书院是以儒教为主的东洋哲学古典读书会,是日本的第一个以王阳明命名的书院,大場先生于其中担当中坚讲师,搞讲座、读书会、和市民举办活动(「王陽明の詩と思想」千葉県漢詩連盟主催・於市川市八幡地区ふれあい館・2015年)。
序言
王阳明(1472-1528)思想中最具特色的部分,在历经漫长精神煎熬后达至的龙场大悟时已然基本成型。此后直到离世的20年间,未看到超过龙场大悟的新的见地。或许有人会说良知学说难道不是新的境界吗?以良知学说的提倡来判准达到新境界,有如此思考者,那是不对的。《阳明先生遗言录》中有言:
先生尝曰:“吾良知二字,自龙场以后,便已不出此意。”[2]
此外,在“阳明先生年谱序”、“刻阳明先生年谱序”(均收录在《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六“年谱附录”)中,钱德洪、王龙溪也有评述:“先生良知之旨于龙场已然悟到”。[3]《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之类的作品暂置不表,就连主张良知学说为较早提出的黄宗贤也未曾说阳明是因龙场大悟而发现良知学说的,更未见其积极谈论良知学说的迹象。那么,为何他们在说到龙场大悟时会出现“良知”一词呢?按正常思维,只要没有用“良知”这个概念进行的思维活动,就不可能表明在提倡良知学说。在他们的意识里,或许是将龙场大悟的内容原原本本续接到良知学说上来理解的吧。钱德洪的“刻文录叙说”中的“学之三变、教之三变”就是说的这事。良知学说的提倡、致良知的宣扬是“教”的最终形态,换言之,只是宣教因大悟而完成的“学”之表达上的变化。因此,龙场大悟的内容,不管良知学说提倡时间的先后,业已统括了37岁至57岁之间王明阳的全部思想。用阳明自己的话即“学的头脑”、“主意”,这些全都是在指这个大悟的内容。
果然如此,就有一点要注意:阳明所说的心即理、知行合一、诚意、立诚、立志、致良知这类的概念理应同龙场大悟结合起来,并且从这些概念中抽象出来的共通主旨才是大悟的内容。当时致良知并未超过其他概念处于优先地位,说到底是因为“致良知”在当时最能明确表达大悟的内容,并且还没有出现增加其他概念的征兆。
然而,在阳明学研究中存在以下问题:将龙场大悟仅限定在悟到了心即理[4];过小评价大悟导向良知学说的连续性的问题;从大悟及至各个概念的派生和从各个概念回溯到大悟视角下的阳明思想核心内容探讨;可以这些人们都不太关注。
这些问题很大程度地扩充了后面的良知学说,包括心即理之下各个概念解释的范围。可称为那些扩充范围的本源之心从“如孝一般真诚恻隐的真情”[5]扩展到“作为从全部制约中解放出来不被任何物所束缚之主体的心”,扩充范围很大。笔者看来,后者的解释预设了作为近代可能性的心之主体性或超越孝悌忠信之道的普遍性的实现,引发了基于此的以三教一致为主要目的之议论,即意欲找到脱离阳明本人而主观臆断的阳明思想的行为,用这种可称为隔离文本式的方法来分析阳明思想,不能认为它具有效性。阳明为再次提倡当然之事(如孝一般真诚恻隐之真情的普遍性)创出新奇言论,无非是他处在无法切身感悟当然之事的状况下,为切身感悟所创的一种方法。言论虽然新奇,就被牵扯进多样发展的可能性甚至连目的都被说成是新奇的,持此论者则过于性急了[6]。
因此,为了牢牢把握前述派生和回溯视角下的其思想核心追求的基础,本文拟以《年谱》为根本,寻着阳明到龙场大悟前后的足迹,参照《传习录》上卷以及徐曰仁所录的十四条等文献资料,考察经由此路径所见的大悟的内容。
二、挫折体验——挫折于什么?
据《年谱》记载,阳明最初立志做圣贤是十一岁。从其周边相关记载看,当时阳明对圣贤的理解还未成形,受别人话语触发,每次读书时他都要静坐凝思,内心暗下誓言:“登第恐非第一等事,唯读书学圣贤耳。”[7]十五岁出居庸关向夷狄学骑射,心仰伏波将军马援,立志专攻四方经略,表现出对社会强烈的关心。此时,或许阳明认为心的完整性与事功这两项才是做圣贤的必要条件。亦或正如“阳明五溺”中的一个能列举骑射一样,阳明认为事功与做圣贤没有太大关系。总之,阳明从幼年开始就血气充盛,才气焕发。他有一段自序:“某,平日亦有傲视行辈,轻忽世故之心。后虽稍知惩创、亦惟支持抵塞于外而已。及谪贵州三年。百难备尝,然后能有所见。”[8]此时阳明还是少年意气,只是对圣贤莫名的憧憬,很难说已有后来所涉之真正的问题意识。
但是,同样是十一岁,他任才恣意所作的《蔽月山房》一诗,以及为先前的理想所花之功夫,看到这些我们就能知道他为究明心(意识)没少费思量。
十七岁结婚时,他竟然离开婚礼宴席去和道士谈论养生之道直至清晨。阳明对长生之道产生兴趣就始于那时。相较而言,他更热衷书法,甚至到了将馆舍里的纸全都用尽的地步。下面有他对格物体验的记录:
(先生曰):“吾始学书,对模古帖,止得字形。后举笔不轻落纸,凝思静虑,拟形于心,久之始通其法。(略)(读程明道的话)乃知古人随时随事,只在心上学,此心精明,字好亦在其中矣。”后与学者论格物常举此体验为证。[9]
上面可看作是此后几年中提倡的有关格物解释的原型,替换成简洁的表达“格物即为正心,心正便能物格”也无不可。奇怪的是,现行的《王文成公全书》中几乎没有讲述这段经历,却记录着“经常举此例以充证据”。《年谱》是一本以钱德洪为中心,举王门弟子总力编纂而成的。《全书》中文牍收录的取舍也是王门内弟子们共同商议,以钱德洪为首而进行的。虽然《年谱》中几乎没有类似逸闻的内容很不自然,但至少应该不说“常引为证据”。记述内容如果准确,这种体验也只是在实际教学中作为例证而常被使用,最多不过是作为援用的例证。因此,与其他例证一同省掉似乎不妥。如果是这样,这个说法与有关格物的《全书》记载的别的说法相比,作为教法的价值就不能被肯认。换言之,这句话是指学习者做功夫时有不足的地方。同理可知,阳明如果以此体验自满自足,那么第二年他和娄一斋会面的意义就没有了。
翌年,与娄一斋会面,令阳明感触最深的是在谈论格物时娄一斋告诉他“人通过学习定能成为圣人”。谈话中特别论及格物可能是因为阳明自己在书法中早有了格物的体验。直至大悟前,阳明对学问的问题意识,已全部归结在格物中了。如果阳明仅满足于前几年在格物体验上的所得,他就没有必要在与娄一斋的会面中为学问上的新知见而感动。在前几年的体验中,关于物与心的关系,阳明虽然体验到了格心即能获得物理,但是他可能并不明白物理,即漂亮的字体之类的是如何与圣人相结合的,阳明的缺如就在这里。阳明前几年感佩于明道,今年又为一斋所触发,他在今后应掌握的科举内容之《经》、《子》、《史》中查阅出典,对自己喜欢开玩笑这点进行反省并开始沉默少言,还收集朱子的书籍广涉研读。如上阳明之所为表明了他所追求的圣人皆是圣学、儒家伦理的体现者。阳明在先验的理中所期待的内容是伦理,娄一斋告诉他通过格物保证能获得伦理,由格物所获之物理与伦理是融合相即的。这才是阳明所求的,同时他不满足于物理,在其中求伦理,这说明没有伦理物理在心中也没有意义。娄一斋所做工作让阳明自觉到物理中伦理才是关键。在心与物的关系中加上儒教伦理,开始促成阳明的领悟。把握了这个端绪的阳明顿涌成圣之意,这和他分别在二十一、二十七岁时所遭遇的挫折是紧密联系着的。
一天,阳明思考着先儒所说一言——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阳明官官署中多竹。即取竹格之,沉思其理不得,于是病倒。由此阳明认为人分为能成圣贤之人和不能成圣贤之人,遂了断成圣之念,转而随顺世俗专研辞章。[10](二十一岁)
此前探求虽宏阔博大,却未能循序精研,故求之未得也无可奈何。后悔之余,决意依循次第,澄心静虑。然而,物理与自心终究分离为二,长时沉郁其中反复思虑至旧病又发。因此,更加认为人可分为能成圣贤之人和不能成圣贤之人。偶尔听道士谈论养生之道,终于决定抛弃世俗入山修行。[11](二十七岁)
关于“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这句话,阳明强调以前的探究未能循序精研,由此可知,他似乎欲从朱子的主张中切割出来独自把握。既然一草一木涵至理,偶尔使用生长着的竹子一气精研想必也能获得至理吧。王阳明读书中,不是从全体的脉络来解读每篇文章的意思,而是参照自己内心固有的基准赋予意义,这样的例子很多。从《全书》中引用文例的解释可以得知,没有什么比《朱子晚年定论》的编集更能如实地反映这样的情况了。[12]比起文献批判,强调直接进入书法领悟精神的王阳明来说,做出这样的行动本身并非不自然。想靠独自领悟文章的内容这种方法姑且不论,靠“格竹子(物)沉思其理”的方法,不能格出真理的话,就应该摸索第二个方法。虽然病倒了,阳明仍然坚持,即使《年谱》的年数有误差,既然他能从失败中拓展出相当的空间,就必须看到阳明对这个方法本身很有自信。[13]此处我们就能看出,前面阳明对书法的探求和跟娄一斋会面等事记载于《年谱》中的意义了。
书法体验给阳明带来了在追求正心的同时能够获得物之理的确信。加之在与娄一斋的会面中,看到了以圣学的方法论(读书穷理),通过格物习得伦理成圣成贤的希望。此时阳明开始的圣学之路也并非完全否定了先前体验的方法本身。格物的原型已在书法的体验中形成,将圣学的方法论适用于此,格物作为获得伦理的方法发挥作用,这样就能成为体认包含伦理的物理之圣人。“物格思其理”的次第与由“凝思静虑”所通达书法之理的过程是完全一样的。所以,一草一木皆涵至理,通过读书、书法的方式来进行穷理,不也能获得至理吗?阳明遵循此路也不是不自然。
可是,至理不会总是对临竹之心显现。阳明直至二十七岁不管以什么为材料,总也不能完全领会把握伦理。当时对阳明来说理是在心外的,所以“心物二分、润泽于心”这样的语句正表明了阳明欲于心中求理。探求书法之理是自己对外单方面的作用,于此相对,探求竹之理则是自己与外界并列相向、各无交集。从结论上看,前者是修养论的核心,因为和后者混同招致挫折。这个问题到“龙场大悟”才得到解决。
总之,阳明的挫折体验是,他对格物的原型、对伦理的获得坚信不疑,确信由此成为圣人的方法论可以成立。但是作为最重要的效果之伦理的习得却完全没有实现。既然对方法论没有怀疑,那么不出结果的理由只能归咎到修养者的努力和素质,所以他必须要坚决推翻“圣人有差别”的说法。
三、悟孝——圣学与异端的分水岭
至龙场大悟前,阳明主要沉迷于佛、老、辞章。[14]从挫折到复归,以上诸道相继登场,但所有这些都没有满足阳明的追求,最后都被一一舍弃。选择辞章是由于阳明原本擅诗文,又因与李梦阳、何景明等交好,遭受挫折之际投身世俗不得已而为之的;对佛老的期待则是要获求内心绝对的境界。
筑室阳明洞中,行导引术。久之,遂先知。(中略)久之悟曰:“此簸弄精神,非道也。”(三十一岁)
已而静久,思离世远去惟祖母岑与龙山公在念,因循未决。久之,又忽悟曰:“此念生于孩提。此念可去,是断灭种性。”[15](同)
以上两段,前者是对老、后者是对佛的见解。前者修炼到了身具预知能力,却视为“簸弄精神”;后者则以“断灭种性”加以拒斥。那么,到底佛老中何物危害心灵呢?三十三岁著《山东乡试录》,其中有策问:“佛老为天下害,已非一日。”“天下之道一而已矣。而以为有二焉者道之不明也。”“夫子之道明,彼将不攻而自破。”“佛老独其专于为己而无意于天下国家。然后与吾夫子之格致诚正而达之于修齐治平者之不同耳。”[16]策问旨在批判圣学内部的堕落,同时也严拒跟佛老的妥协。此后又对喜好佛老、反复试图推进三教合一的自己门下弟子萧惠、王嘉秀如下指教:“吾亦自幼笃信二氏,既谓自有所得,谓儒者为不足学。其后居夷三载,见得圣人之学若是其广易宏大。始自叹悔错用三十年气力。大抵二氏之学、其妙与圣人只有毫麾之间。汝今所学,乃其土苴。辙自信自好若此。真鸱鸮窃腐鼠耳。”[17](王嘉秀以为:圣学的最高处以心的清澄为目的,佛老也相同,故可资参看,较圣学中落于卑俗者更具纯粹性。针对王嘉秀此说,)阳明回应道:“若论圣人大中至正之道,彻上彻下,只是一贯,更有甚上一截(上达、心之清澄)、下一截(下学、伦理)。”[18]而对喜静的陆清伯又答道:“只说明明德而不说亲民,便似老佛”。[19]本文阳明的异端观不是主题,不做详述。作为儒者的阳明之佛老批判没有明显的理论展开,但是如果论及圣学与异端之分歧,在阳明处二者可谓天壤之别,原本我们也知道阳明判佛老有害的理由的分量。
这个分歧点指的是伦理。这个伦理正如“修齐治平”、“亲民”一样,是存在于人与人的联系中的道。这个人生当行之道是如此的真切却又难以实行,即使经书中早有明示,阳明也难深信。通过自觉到自己与生俱来的对亲人的思念,深切感受到这虽是日常身边小事,可它非常重要。阳明认为问题的解决寓于对亲人的思念中,佛老却对其有损。阳明这番见解,反观其里,表明了他将佛老的开悟理解为是极端地限定在个人内部的东西,它存在于一味遮断外物,感受不到伦理的状况之下。所以,对阳明来说伦理即全部圣学的领域,悟孝则让其导向圣学。感到在圣学中遭遇挫折的阳明寄希望于佛老来解决自心的问题,但是,心的绝对境地的获得无法在视伦理为困惑的佛老之伦理中得以实现。阳明在对亲人的思念中感觉得救,是因为他从无法停止的孺慕之情中感受到了实在(伦理)。意欲要舍弃全部,仍会残留对亲人的思念。这种纯粹的心即是孝心,在伦理中纯意识的心里,阳明理解到了心的绝对的境界。有了这种自觉后,阳明即刻向耽于坐禅的僧侣们说孝,让他们改变信仰。这一轶事说明了阳明认为孝的自觉有等同于大悟的重要性。
为进一步佐证这个观点,《传习录》上卷徐曰仁所录部分中,在论述工夫时,以把对亲人的思念推向究竟的孝心为线索,试图使心恢复至天理这样的条目占了一半。具有代表性的是第三条。
冬温也,只是要尽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间杂。夏同上。(中略)这都是那诚孝的心发出来的条件。却是须有这诚孝的心,然后有这条件发出来。[20]
不符合的条目都是不关乎工夫的条目,将六经是史、唐虞三代的治、文中子评价的条目的因素考虑进去,这样一来关于工夫的说教可以说大部分都出现了孝,表明了阳明把孝认为是最容易发现的理,同时也说明了他三十一岁时的悟孝是何等重要。此外,这些都是有关工夫的条目特别是有关格物的条目,考虑到这些悟孝与一直以来的摸索不是没有关系,至少在阳明的意识里,悟孝对格物的考察即阳明的学问观作为一大契机映现了出来。但是,说到底孝只要限定在与亲人关系中天理的发现,就不可能全盘适用于处在社会关系下的自已的心的状态。因此,阳明赞同明道之言——“孝是行仁之本,非仁之本”。[21]就算悟到了孝,阳明感觉仍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至此,自己从一开始思考、摸索,一步一步领会来的内容,到了大悟才开始相互关联、起作用并开花结果的过程是我们在看大悟的内容时应给予关注的。所谓大悟,就是以格物为核心,通过学问欲成为圣人(伦理)之体现者的王阳明在切实的精神磨砺中不断累积起来的内容之集大成。
四、龙场大悟——圣人之道,吾性自足
纵观到目前为止的经过,可以总结几点:对阳明来说,做学问是为了成为伦理的体现者——圣人,这里的学问与格物同义;格物已成为在自心中领悟伦理的手段;只有在伦理中承认作为理的存在,想努力把握它,可客观的物理不与伦理直接相连即理不能在心中有任何切身感受因而陷入死寂;理由心外向内获取,曾一度放弃对伦理的把握,通过悟孝又在自己纯然状态下真切地感受到了理,但这同时也给人带来不能让人开阔视野获得全体的理之烦恼。
以上这些在龙场是如何得以解决的呢?
下面记录的是三十七岁被贬谪龙场遭受困厄的阳明的情况:
时瑾憾未已,阳明“尽性,俟命”[22]般地反复思考,自计得失荣辱皆能超脱,惟生死一念尚觉未化。乃为石墩自誓曰:“吾惟俟命而已!”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久之,胸中洒洒。而从者皆病,自析薪取水作糜饲之;又恐其怀抑郁,则与歌诗;又不悦,复调越曲,杂以诙笑,始能忘其为疾病夷狄患难也。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中略)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误也。乃以默记《五经》之言证之,莫不吻合,因著《五经臆说》。[23](三十七岁)
黄宗贤的《阳明先生行状》中只是提到,只要在静一中求得生死一念的克服即可大悟,并未记载具体内容。但是《年谱》中的记载与此不同:着力于生死一念的克服是相同的,然能克服生死一念不是在静一中心平气和之时,而是一旦专念于为随从的病自己应该做什么时就能忘记疾病、夷狄的艰难,想到圣人除此之外还能做什么时即刻大悟。也就是说,不是在静一中得到解决而是在专注于自己该做之事时的心中得以解决。并且,甚至说了自己曾经戒除的玩笑,想方设法让眼前病倒的随从恢复过来费尽思量,生死一念在其中得以克服。以此心境推度圣人的过程中悟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
《行状》和《年谱》的差异很大,因为按《行状》的说法,如果将意识集中于内面的心,那么心的问题就能得到解决,像随从的病这样的外在的事物与之没有任何关系。这时的大悟是切断了和不断变化的外界之间的关系,将与之一一对应的意识活动认作虚妄加以抑制,在静谧中超越人的最大难关——生死一念之主观方面的动摇,其结果就是获得从主客双方的迷惘处出来的事先可知的主客未分之绝对的境界。但是,这样就与阳明苦口婆心数度提到的“释氏无私心最终是割舍了社会而得到的,这不是私心是什么。”[24]这句话为代表的拒绝异端的主张明显有矛盾。并且如此一来,就和先前的悟孝以及后来对“今见学者渐有流入空虚、为脱落新奇之论。”[25]的批判无法联系起来。对格物的问题意识突然消失,这很不自然。阳明的大悟,不是被搞成了“阳儒阴佛”的王学末流所说的那样超越人伦观念的境界而获得的。
反而,《年谱》中所说的构造更值得注目。这里一度处于静一中使内心安宁,面对眼前事物,采取圣人同样也会如此去做的行动,结果心会完全得到安宁。换言之,在纷扰中使心沉静,如果离本体越近越能接近当为,如此去做本体就是愈加明朗的构造。所谓当为就是伦理。践行伦理,心才不至流于纷扰进而趋于专一,这就是阳明长期探求的心之绝对境界。由此心而发,究明此心的行为即是格物。这不是超越主客后出现的主客未分之心的状态,而是彻底地专注于自己的伦理意识之心的状态,虽然各个伦理意识状态根据对应的事物有所不同,但是,它是在一以贯之的伦理的框架内持续绵延的心的状态。此外,还需留意阳明参照五经确认自说所著的《五经臆说》。究竟说来,所谓伦理必须是依据经书的儒教伦理,这点不能逾越。故说“圣人之道,悟性自足”。这里的不同即阳明所说的“妙处不同”。“吾性”正是这种专一的伦理意识;对事物专一的伦理意识起作用,亲自做与之相即的行动即能“圣人之道自足”。
上面引用的是《传习录》上卷第三条。孝心真诚发动,孝的细节自然出现,就会与它具有同样构造;“真诚”是指变得专一。有名的《传习录》上卷第三十二条中的“虚灵不昧,众理具万事出。心外无理,心外无事。”也与此完全相同。阳明所谓的性,是根据当场应该发动的伦理意识,迅速采取行动,激活包含直至具像化后的处所之心的作用的状态。
伦理不由外获得,而从内发动,如此一来,所有的都在具体意识中处理,无法严格进行性情的区别,这就是龙场大悟的内容被说成“心即理”的原因。但是,从这个构造上看,把它说成是“知行合一”也好,“诚意”也好,甚至“致良知”也可以。归根到底它都具有这样的结构——由于依此落实到行动的心的功能的激活,工夫会自动发生,结果变成了一个伦理意识之心并作为本体而明确化。
此后,诚意、立诚、立志等相继被提出。即使它们出现也没有否定以前的提法,而是同时并存,这也是因为同样的理由。这个构造就是成为阳明思想核心之龙场大悟的内容。自己和外界在伦理的意识作用下被统合处理(根据伦理的物理的意义化)这一点,就能脱离出一如竹之理这样的自己与外界的分裂状态。另外,就中我们也能看出一点,这点从大悟后教学的混乱上面亦可窥之。大悟过后不久提倡的知行合一的教法,使弟子们被知行论所束缚产生了混乱。为打开局面,使他们感受龙场体验,阳明让弟子们静坐。这样也没有使他们从静坐达到大悟,只是停留在静坐,无有进展。无视外在事物只重内心,飘游于高远空虚,结果出现了趣向禅佛的弟子而告失败。
为什么会失败呢?是因为如前所述阳明对佛老的批判一样,对阳明来说,不带着伦理把握的内心安稳是虚幻的之缘故。追究原因,是作为伦理把握手段的格物应该如何才能发挥作用;阳明的问题意识之前先有大悟,这段经历一部分弟子不理解,一味将意识缘去向本体所致。从阳明的佛老批判以及后来的龙场大悟上看,不面向社会的自我意识如果不专一于伦理,本体最终是见不到的。考虑到阳明的修养论是在本体的机能活性化的工夫下的自动发生、工夫完成后本体的明确化,附在《传习录》上徐曰仁的文章末尾有言:“格物是诚意的功夫,明善是诚身的功夫,穷理是尽性的功夫,道学问是尊德性的功夫,博文是约礼的功夫,惟精是惟一的功夫。”正如此番论述所言,使功夫发挥作用的本体与本体明确的具体手段之工夫相即相融,同时又以专一于伦理意识为目的,必须不偏向任何一方保持平衡。这也是心与社会(外物)相即的平衡。这就是前面所说的“圣人之道上下一贯”。保持这种平衡必须要明确认识到格物是把握伦理的手段,心(明明德)和社会(亲民)要密不可分割。有了这些,存在于人们心中的以通过伦理的物理之意义为主轴的修养论才有生命力,将伦理限定在儒教伦理上的意义与大悟的内容才同样重要。

注释:
本译文系2012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日本近现代哲学的转换研究”(12XZX014)的阶段性成果。
[1]译者简介:胡嘉明,贵州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西田哲学、日本阳明学;潘承健,贵州大学哲学学院中国哲学2015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阳明学、西田哲学。
[2]《遗言录》第二十四条“先生尝曰:吾良知二字,自龙场以后,便已不出此意。”同样的语句也出现在《刻文录叙说》中。
[3]“为养生之术,(中略)然即之心,若未安也。复出而用世。谪居龙场,衡困拂郁(忧),万死一生,乃大悟良知之旨。(中略)即三圣所谓中也。”(钱德洪《阳明先生年谱序》)“渐渍于老释,已乃折衷于群儒之言,参互演绎,求之有年,而未得其要。及居夷三载,动忍增益,始超然有悟于良知之旨。”(王龙溪《刻阳明先生年谱序》)
[4]安田二郎将心即理作为“阳明学的真髓”定位贯穿阳明一生的根本思想(《中国近世思想研究》,弘文社,一九四八年),笔者所说的大悟是指心即理就是站在安田的立场来说的。
[5]在《宋明时代儒学思想的研究》(广池学园出版部、一九六二年)一书中,楠本正继认为“以真诚惻怛的良知的真切,笃实的发现即是孝悌”, 把良知作为“活动着起作用的心以及道德法则,所谓和理的合一形态,心与道德相一致去实现的立场。”。这里的心确保了主体性的同时,再次确认了自己道德的价值,不被任何外物所纷扰的心处于对极之一方。借用阳明的话表达,后者即是不被束缚的私心。
[6]如上所提到的楠本的书、冈田武彦《王阳明和明末的儒学》(一九七〇年,明德出版社)的书中,他们皆以,为体验儒教伦理的修养论提倡良知论的邹东郭、钱德洪、欧阳南野等所谓的“修证派”,是王学正统的继承人,不是想要超越儒教理论的“现成派”。两位观点符合本稿主旨,笔者完全赞同。
[7]“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二《年谱》十一岁)
[8]“某,平日亦每有傲视行辈,轻忽世故之心。后虽稍知惩创、亦惟支持抵塞于外而已。及谪贵州三年。百难备尝,然后能有所见。”(同上,卷四《文录》《与王纯甫》一、四十一岁)
[9]“吾始学书,对模古帖,止得字形。后举笔不轻落纸。凝思静虑,拟形于心。久之始通其法。既后读明道先生书曰:“吾作字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学。既非要字好,又何学也,乃知古人随时随事,只在心上学。此心精明,字好亦在其中矣。后与学者论格物,多举此为证。”(同上,卷三十二《年谱》十七岁)
[10]“一日思先儒谓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官署中多竹。即取竹格之,沉思其理不得。遂遇疾。先生自委圣贤有分。乃随世就辞章之学。”(同上,《年谱》二十一岁)
[11]“悔前日探讨虽博,而未尝循序以致精。宜无所得。又循其序思得渐渍洽浃,然物理吾心终若判而为二也。沉郁既久,旧疾复作。益委圣贤有分。偶闻道士谈养生,遂有遗世入山之意。”(同上,《年谱》二十七岁)
[12]但是并不是对全部的文本都采取这种态度。正如山下龙二《阳明学的研究》(现代情报社,1971年)、水野实《王守仁的‘诚意’宣扬的基础》(《东洋思想与宗教》1997年)中详说的那样,在《大学》的解释中重视诚意是准确地吸取把握了《大学》的本义。
[13]《传习录》下卷,第一百一十八条中记载:“众人只说格物要依晦翁。何曾把他的说去用。我着实曾用来。(中略)因指亭前竹子令去格看。”此后也没有对这种方法产生过怀疑。
[14]参照《传习录》徐曰仁序文。
[15]“筑室阳明洞中,行导引术。久之遂先知。久之悟曰:“此颠弄精神,非道也。”又屏(摒)去。已而静久,思离世远去,惟祖母岑与龙山公在念,因循未决。久之又忽悟曰:“此念生于孩提。此念可去,是断灭种性矣。”(《全书》“年谱”三十一岁)
[16]“天下之道一而已矣。而以为有二焉者道之不明也。”“夫子之道明,彼将不攻而自破。”“独其专于为己而无意于天下国家。然后与吾夫子之格致诚正而达之于修齐治平者之不同耳。”(同上,卷三十一之下,《山东乡试录》)
[17]“吾亦自幼笃信二氏,自谓既有所得,谓儒者为不足学。其后居夷三载,见得圣人之学若是其简易广大。始自叹悔错用三十年气力。大抵二氏之学,其妙与圣人只有毫厘之间。汝今所学,乃其土苴。辄自信自好若此。真鸱鸮窃腐鼠耳。”(《传习录》上卷第一百二十五条)
[18]“若论圣人大中至正之道,彻上彻下,只是一贯,更有甚上一截下一截。”(同上,卷第五十条)
[19]“只说明明德而不说亲民,便似老佛。”(同上,卷第九十条)
[20]“冬温也,只是要尽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间杂。夏清也,只是要尽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间杂。(中略)这都是那诚孝的心发出来的条件。却是须有这诚孝的心,然后有这条件发出来。”
[21]参照《传习录》中卷“答聂文蔚”。
[22]附录在佐藤一齐的眉批之后。
[23]“时瑾憾未已。自计得失荣辱,皆能超脱,惟生死一念尚觉未化。乃为石槨自誓曰:“吾惟俟命而已。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久之,胸中洒洒,而从者皆病。自析薪取水作糜饲之。又恐其怀抑郁,则与歌诗。又不悦,复调越曲杂以诙笑,始能忘其为疾病、夷狄、患难也。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乃以默记五经之言,证之,莫不吻合。因著五经臆说。”(《全书》“年谱”,三十七岁)
[24]“又问,释氏于世间一切情欲之私都不染着,似无私心。(中省略部分)曰,亦只是一统事。都只是成就他一个私己的心”(《传习录》上卷第九十五条)诸如此类的主张前后都有出现。
[25]“今见学者渐有流入空虚,为脱落新奇之论。”(《全书》“年谱”,四十三岁)
转载来源:“西田哲学研究”公众号 2022-11-26
编发:中国文化书院(阳明文化研究院)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 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