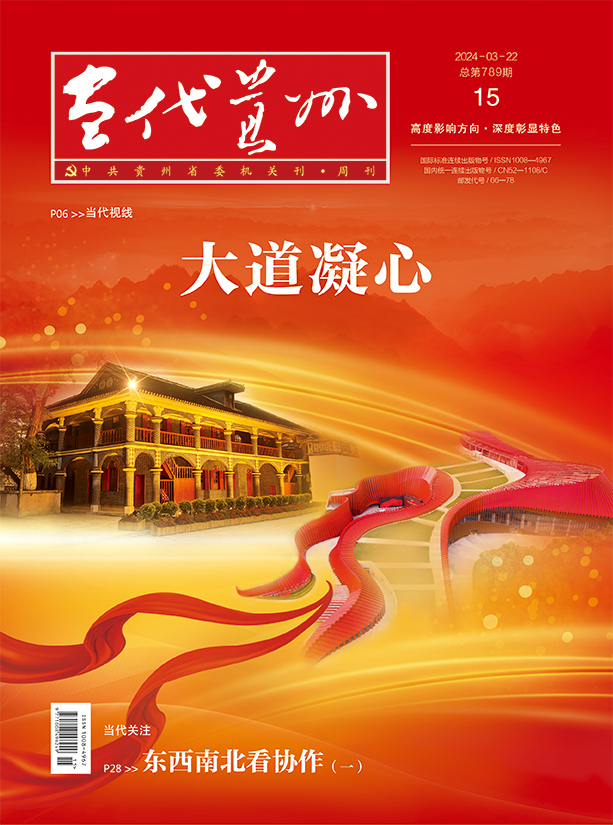

作者:陈彦
提要:本文通过对龙场悟道的诸多原始史料进行分类、梳理和解读,试图找出诸史料所提供的龙场悟道原初理论信息的晦暗与思想张力之所在,从而还原龙场悟道所蕴含的理论勃勃生机。
龙年,龙腾虎跃新气象,在文化领域,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光辉旗帜,正不断指引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而阳明文化作为贵州的特色文化名片之一,如何不断保持阳明在黔思想的文化先进与活力,保持其理论探索的可持续与发展性,不仅对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也能不断夯实贵州优秀文化的比较优势。
正德三年(1508年)11月的龙场悟道中,王阳明先生“所悟”究竟为何,其实未有严格的确论。就学界而言,有强调此间阳明所悟为“良知学说”的,以近代大儒钱穆先生为代表;也有强调龙场悟道的关键乃是悟出了“心即理”的,持这种说法的包括许多著名学者,如陈来、杨国荣、吴震、王路平等先生学人;还有强调所悟为“格物致知之旨”的,如陈立胜先生;当然,更有从“见道”“本体、工夫”或“本体与实践”的结合,来“整体”体认龙场悟道的,如民国大思想家徐梵澄、贵州知名学者张新民先生,以及阳明研究的当代泰斗束景南先生,等等。其实,细观这些分歧,既来自龙场悟道原始史料记载的差异,也有来自后世学人对龙场悟道原始史料的理解取径的不同。
笔者尝试将龙场悟道的原始史料中的张力问题,加以适当呈现,以为贵州当代阳明研究的不断发展,提供一点微不足道的思想助力。
龙场悟道的原始史料,今天为大家所熟知的,至少有3个重要的早期史料渊源,分别来自王阳明的弟子黄绾、钱德洪,以及王阳明的自叙。虽然这几处史料早为学界所识,但为了更好地辨析龙场悟道的相关阐释的分歧所在,笔者在此再次引述辨析。
同道叙述:黄绾《阳明先生行状》
首先是与王阳明共倡圣学的同道,亦是后来的弟子黄绾的叙述。黄绾在其《阳明先生行状》中,曾如是记录阳明在正德三年冬至发生的这次悟道经过:
“日夜端居默坐,澄心精虑,以求诸静一之中。一夕,忽大悟,踊跃若狂者。以所记忆《五经》之言证之,一一相契,独与晦庵注疏若相牴牾,恒往来与心,因著《五经臆说》。”
为了更贴近龙场悟道的真实经过,我们必须谨慎小心阅读和提炼出原始史料的可靠信息,尽量不做任何超出原始史料的引申和发微。秉承此原则,从上述文字中,我们可以读到的确凿信息,止于如下两点:(1)该次悟道之所得,同朱子(晦庵)在儒家经典注疏中的阐释,在理论上正相对立;(2)所悟之道,可用来贯通对五经的理解,而阳明正是基于此,写做了《五经臆说》,作为本次悟道的理论总结。
原始史料:钱德洪《阳明先生年谱》
第二处龙场悟道的原始史料,是大家所熟知的钱德洪《阳明先生年谱》中的记载,据其所述:
“三年戊辰,先生三十七岁。春,至龙场。先生始悟格物致知。龙场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棘中,蛇虺魍魉,蛊毒瘴疠,与居夷人鴃舌难语,可通语者,皆中土亡命。旧无局,始教之范土架木以居。时瑾憾未已,自计得失荣辱皆能超脱,惟生死一念尚觉未化,乃为石椁,自誓曰:‘吾惟俟命而已!’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久之,胸中洒洒。而者皆病,自析薪取水作糜饲之;又恐其怀抑郁,则与歌诗;又不悦,复调越曲,杂以诙笑,始能忘其为疾病夷狄患难也。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窹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乃以默记五经之言证之,莫不吻合。因著《五经臆说》。”
从该史料文本中,我们能读到这样一些从钱德洪的理解出发的确凿信息:(1)这次悟道的内容是关于“格物致知”的,或名为“格物致知之旨”;(2)该次悟道的理论内涵,可进一步引申出:悟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3)所悟之道,可以贯通五经,故而阳明创作了《五经臆说》。
但是,需要提及的是,钱德洪在《阳明先生年谱》中,实际还提到了和龙场悟道近乎同一时期的另一次悟道,此即《年谱》所记录的发生于次年即正德四年(1509年)的一场名为“知行合一”之悟:
“四年己巳,先生三十八岁,在贵阳。提学副使席书聘主贵阳书院。是年先生始揭知行合一。始席元山书提督学政,问朱陆同异之辨。先生不语朱陆之学,而告之以其所悟。书怀疑而去。明日复来,举知行本体证之《五经》诸子,渐有省。往复数四,豁然大悟,谓:‘圣人之学,复睹于今;朱陆异同,各有得失,无事辩诘。’遂与毛宪副修葺书院,身率贵阳诸生,以所事师礼事之。”
如是,根据《阳明先生年谱》的记载,发生在贵阳或龙场的悟道,很可能包含前后两个阶段:作为“格物致知”的前悟和“知行合一”的后悟。尽管这两个阶段的悟道时间间隔很短。因为据考证,“知行合一”之悟,乃是王阳明接受讲学之邀,对当时贵阳提学副使席元山所讲述的。从时间发生来看,大致介于正德四年的十月到十二月之间,比之“格物致知”之悟晚一年。但考虑到王阳明很可能事先就完成了“知行合一”之悟,而后才接受的文明书院的讲学邀请,因此,我们可以大胆认为:钱德洪所记载的发生于正德三年和四年之间的所谓两次悟道,实际发生于短短的一年之内。(参见张明、管华香:“王阳明与贵州贵阳”,网址:http://acc.gzu.edu.cn/2019/1226/c5673a130254/page.htm)或者可以说,我们难以分清到底龙场悟道是一次完成,还是分两个阶段才完成,或者说,是否“格物致知”之悟不同于“知行合一”之悟,或者说两者本就属于同一次悟道,只是阳明在不同场合所谈论之侧重点不同。——此即钱德洪的记载所留给后人的有关龙场悟道的谜团。
自身说法:四处文本涉龙场悟道
第三类原始史料,来自王阳明自身的说法,至少见于如下4处文本。首先,第一处文本来自钱德洪的转述。在《刻文录叙说》中,钱德洪如是转述了王阳明谈到自己当时贵阳讲学时的情形:
“居贵阳时,首与学者为‘知行合一’之说……先生尝曰:‘吾始居龙场,乡民言语不通,所可与言者乃中土亡命之流耳,与之言知行之说,莫不忻忻有入,久之,并夷人亦翕然相向;及出与士夫言,则纷纷同异,反多扞格不入,何也?意见先入也。’”
这段话中,王阳明并没有特别提到发生在贵州的特别的悟道经历,而是提及了此间无论在龙场驿还是贵阳的文明书院,当面对普通乡民和流放的中土之民,亦或贵阳的士大夫们,自己皆阐发了一种被称为“知行之说”的理论。或者说,王阳明在贵州期间,所主张的乃是某种“知行”理论。由此,我们似可顺理成章地认为:若存在龙场悟道的事实,那么王阳明此间所悟之道,即是某种“知行之说”。
接下来的3处阳明龙场悟道的自述,包括其在《朱子万年定论序》《阳明先生遗言录》《传习录》等各处的言论,我们分别摘录如下:
“其后谪官龙场,居夷处困,动心忍性之余,恍若有悟。体验探求,再更寒暑,证诸《五经》、《四子》,沛然若决江河而放诸海也。然后叹圣人之道坦如大路,而世之儒者妄开窦径,蹈荆棘,堕坑堑,究其为说,反出二氏之下,宜乎世之高明之士厌此而取彼也,此岂二氏之罪哉!”(《朱子万年定论序》)
“后至龙场,又觉二氏之学未尽。履险处危,困心衡虑,又豁然见出这头脑来,真是痛快,不知手舞足蹈。此学数千百年,想是天机到此,也该发明出来了。”(《阳明先生遗言录》)
“吾亦自幼笃志二氏,自谓既有所得,谓儒者为不足学。其后居夷三载,见得圣人之学若是其简易广大,始自叹悔错用了三十年气力。大抵二氏之学,其妙与圣人只有毫厘之间......惠惭谢,请问圣人之学。先生曰:‘汝今只是了人事问。待汝辨个真要求为圣人的心来与汝说。’”(《传习录》卷上103)
以上3处,合而言之,王阳明强调了自己在贵州“居夷”期间所“豁然”之理和二氏之学的某种亲似与相契。而在《传习录》卷上103处,他更进一步强调,二氏之学和儒家圣人之学之间的近似,而近似的关键点在于体悟“圣人的心”。该语可谓一语点破王阳明所理解的二氏之学和儒家圣人之学的相契之真谛,故而,总结上述3处言论,我们得到如是讯息:王阳明自述的龙场悟道,乃是回到二氏与儒家圣人都朝向的“圣人的心”。
对史料信息做更为融贯、综合的解释
综合上述3类原始史料所给出的有关龙场悟道的文本讯息,我们将各类讯息加以提炼,并概括出此间所悟之道的相关理论特征,分别如下:
一是该悟道关乎某种“格物致知之旨”;二是该悟道关乎某种“知行之说”;三是该悟道导向诸家所共契的某种“圣人的心”,从而通向“悟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四是该悟道同朱子的相关阐发正相对立;五是该悟道可用来贯通对五经的某种理解,并在此基础上,王阳明写成《五经臆说》一书。
但是,从龙场悟道的原始史料得出的这5条所悟之道的理论特征,相互之间其实并非完全融贯合一、清晰明了,而是存在理论张力的。比如我们之前所阐发的:“格物致知”和“知行之说”究竟是一次悟道的内容,还是某一段时间中先后发生的两次悟道?此外,学界对《五经臆说》同龙场悟道之间的关系,也存在疑问,即《五经臆说》的写作究竟是龙场悟道的结果,还是起因?因为从当下学界的时间考证来看,《五经臆说》的写作实际早于龙场悟道,即自正德三年四月,王阳明来到龙场驿,并筑玩易窝之后就开始写作此书,一直到离开龙场驿才大致完成,前后经历了19个月左右。(束景南:《阳明大传:“心”的救赎之路》上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430页)
因此,《五经臆说》是否如阳明弟子所言,乃是龙场悟道之后的产物,或许并非确凿。尽管今天《五经臆说》只剩下序言和13条片段,我们无法窥知其全貌,但仅从《五经臆说》写作的时间跨距而言,假设阳明在经历龙场悟道后,对之前的《五经臆说》文稿进行了修订和补充,从而让《五经臆说》彻底成为龙场悟道的产物,亦属解释得通。
从上,我们可以看到,龙场悟道的原始史料,其实正好为后来者的阐释提供了丰富而充满张力的思想源泉。无论后世将龙场悟道解释为“良知学说”之悟,还是“心即理”之悟,亦或“格物致知之旨”之悟,其实都源于对龙场悟道原始史料的部分运用。这也提醒我们,如何对史料信息做更为融贯、综合的解释,或化解其间的矛盾,或澄清之间的分歧,尤其“格物致知”和“知行之说”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合一”的可能性,或理论的统一性?沿着这些思考路径,或许能为我们进一步敞开阳明心学的贵州魅力,并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光辉指引中,去追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博大精深所在。
作者系哲学博士,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副教授
本文为贵州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阳明心学与贵州文化传承研究(2023GZGXRW118)”阶段性成果
来源:《当代贵州》2024/15 绘图:赵相康 编辑:岳振
一审:王凤梅 二审:何茂莉 三审:张清
编发:中国文化书院(阳明文化研究院)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 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