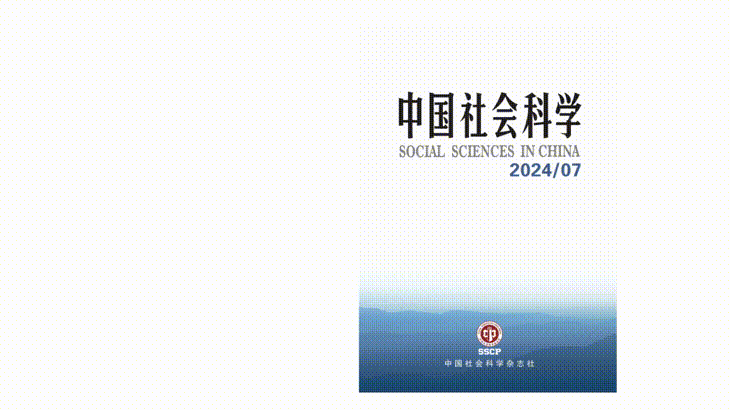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理性贡献
作者:张志强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732)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2023年在中国历史研究院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重申了这一判断,并着重说明:“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个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还特别强调,正是这一点,是召开这次座谈会的原因。这表明,习近平总书记是把文化建设提升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高度来看待的,是把文化建设提升到国本和国运的意义上来把握的。
2023年10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第一次在“宣传思想”之后加上了“文化”,这一变化具有重大的标志性意义。这表明,我们党深刻认识到了文化建设对于宣传思想工作的基础性意义。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宣告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在党的二十大开局第一年,也是开启新征程的第一年,提出的第一个重要思想,是文化思想,这不仅表明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更充分说明了文化思想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基础性或核心性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对文化建设的重视成为习近平文化思想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因此,如何理解文化建设在治国理政中的突出位置,是我们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旨趣,并通过习近平文化思想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性的关键。
一、习近平总书记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文化建设重要性的认识,首先表现为对于精神文明重要性的认识。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精神独立对于民族发展的重要性,特别强调“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就是要促进中华民族精神独立和精神自主。因此,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主题就是文化主体性的建设,就是通过文化建设实现文化自信。另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协调发展,精神和物质的共同富裕。文化建设是促进精神与物质协调发展,体现中国式现代化宗旨的关键领域,是体现中国式现代化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优越性的关键领域。
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文化建设重要性的认识,蕴含着一个深刻的理论突破。这一突破在哲学高度上深化了我们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认识,对于我们在实践中深刻把握经济与文化的关系,摆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的关系,提供了科学指南。
根据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经济基础具有归根结底的决定性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力。一般而言,文化、精神文明都被作为上层建筑的内容,特别是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的内容。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力主要是通过文化,通过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这种反作用力最主要的表现就是通过对经济基础中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实现的。生产关系是人的关系,通过对现实的人的关系的再生产,维持了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因此,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在一定意义上也依靠文化或意识形态对社会现实、对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来实现。经济基础归根结底所具有的决定性作用是长时段、根本性的作用,在具体历史社会条件下,其必须依赖更为复杂和多元的上层建筑因素。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关于文化或意识形态再生产经济社会现实的理论。文化或意识形态对于经济、社会、政治现实的再生产作用,表明文化或意识形态实质上也具有物质性,具有实践的物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充分认识到了文化或意识形态对于经济建设的作用,充分认识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得的伟大成就,是在文化或意识形态的保障下实现的。两者是一种正相关关系。这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一个重要原理性贡献。
坚定文化自信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主题和主线。习近平总书记说,“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文化建设的宗旨就是树立文化主体性。根据西方的现代化理论,现代化是一个社会诸领域分化发展的进程,其中经济发挥着统合社会的作用,这种统合作用的实质是资本驾驭政治,其对社会的统合则不过是通过商品拜物教实现的。因此社会分化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必然。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取得经济长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关键在于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党的领导从根本上超越了经济统合社会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的政治对社会的统合,也需要通过文化领导权来实现。文化建设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实现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的文化建设。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中国共产党通过文化建设树立起的文化主体性,没有强大的文化自我,经济、社会等领域就不会统合为一个实践的总体,诸领域发展取得的成就必定会发生某种反噬,带来社会的分化。坚定的文化自我,是捍卫经济、政治、社会、生态等领域伟大成就的根本保证。正是在此意义上,文化建设保障了经济社会建设,文化领导权也成为政治领导权的根基。
作为“五位一体”之一的文化建设,发挥着统括政治、经济、社会、生态诸领域建设的基础性或中介性的作用。文化建设使得“五位”真正成为“一体”,并使这个“一体”可以继续再生产下去。这正是“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的道理根据,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合为一个体系的关键。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不矛盾。对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关系的全面认识,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辩证思维和系统思维,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理性贡献之一。
二、习近平总书记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重新焕发了中华文化中治理与教化相融合的悠久传统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作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首要政治任务,就是聚焦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实现教育人民的政治任务,就要让主流价值观成为人民群众日用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成为构造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价值力量。日用不觉意义上的共同价值观念,就是已经成为良知良能的价值本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这表明作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已经是具有中华文化生命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相贯通、与人民群众日用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相融通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创造人民群众新的生活世界的价值力量。用创新理论教育人民,就是要让创新理论成为日用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这是文化建设的目标,也只有文化建设能够达成这一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认识到文化具有的遍布性和弥散性的特征,具有的日用不觉的特点,认识到了文化作为表意实践在个人与其现实之间发挥的象征纽带作用。因此,把文化作为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手段,用文化来教育人民、凝聚认同,是深刻认识到了文化的教化功能。中华文明中的“治教”关系,是政治与文化在共同目标之下形成的相互支撑、相互成就、相互融合、共属一体的关系,两者虽有功能分工但在共同目标之下统合为一,共同打造出了天下文明的伟大格局。习近平文化思想将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另一个原理性贡献。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24年第7期 P7—P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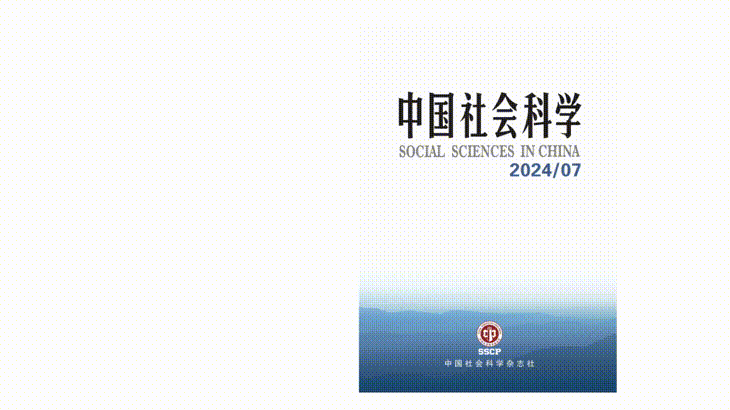
“第二个结合”与文化主体性重建
作者:李文堂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北京100089)
文化主体性问题,是一百多年来中华文化发展道路上不断触及的问题。不同时期的“古今中西之争”,实际都围绕这一问题而展开。这样的问题意识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文化变迁中不断浮现出来,经常出现在理论界的各种争论之中。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进一步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结合”维度,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维度,直接回应并深刻阐释了这个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挥之不去的文化主体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指出:“这一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的;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立起来的。”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主体性的重要论述,是对党领导人民百余年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文化建设成就与经验的深刻理论总结,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推动文化传承与发展、巩固文化主体性提供了思想指导,充分展现了文化自信、开放包容、守正创新的文化主体意识与文化生命力。
文化主体性不是一种封闭的、固守的、僵化的历史规定,也不是套用本土与外来之间的主次、体用关系所能描述的。文化主体性是一种具有文脉自觉、进行自主创造、达到超越维度的文化生命意识。作为文化意义上的坚定自我,它具有历史性、创造性、超越性。没有历史性就没有文化身份认同,没有创造性就没有文化生命力,没有超越性就没有文化主体的理性觉醒,容易停留于经验或地方性知识。
中华文化的现代化有一个文化主体性的重建过程。重建不是推倒重来,而是文化生命的自我更新,以新的文化形态再生。中华文化在殷周之际开始了人文道德觉醒,出现了内在超越意识,形成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并不断自我更新。历史上,周孔所代表的文化生命,经过历史变迁,吸收了佛学义理,以宋明理学形态出现,就是一种文化主体性的重建,体现了中华文化守正创新的生命力。晚清以来,中华文明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文化主体性面临更加严峻而深刻的重建课题。但无论是“中体西用论”,还是“全盘西化论”,理论上都存在严重缺陷,实践上都失败了,因为它们都没有很好把握文化生命的规律。“中体西用论”无法摆脱文化中心主义窠臼,“全盘西化论”则完全丧失了自己的文化主体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则通过“两个结合”激活了中华文明,特别是“第二个结合”激活了中华文明内在的文化生命,有力推动了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重建。
五四新文化运动无论以中国的“文艺复兴”还是以中国的“启蒙运动”来诠释,都代表了一种自强不息的文化生命意识的觉醒。从最后的“伦理觉悟”到马克思主义带来的“伟大觉醒”,构成了一个“觉醒年代”。然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表明,真正的“伟大觉醒”不是一个年代,而是一个漫长的世纪。只有经历一次又一次历史危难,经历一次又一次思想解放,实现一次又一次文化创造,我们精神上才能不断从被动走向主动,走向理性的自信、包容与成熟,我们的文化主体性才能通过“两个结合”而逐步重建,我们才能造就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
那么,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具有这样强大力量推动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重建?首先,因为马克思主义对西方文明与现代性具有批判性、解构性,在克服西方文明的局限、抵御资本主义现代性野蛮、防止文化殖民主义侵入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有利于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重建;其次,马克思主义在批判封建残余文化、肯定科学与民主、揭示现代化规律等方面则可以引领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重建方向;再次,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新人文主义,其文化价值观更符合中国人的文化理想,在其中国化的实践过程中,逐步实现了与中华人文精神的深度融合。
黑格尔说,有文化的民族竟没有形而上学,就像一座庙,其他各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毛泽东同志说,“学”不分中西,基本理论是中外一致的。中华文化具有天下道理的关怀与形而上传统,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将人的意义安放在人世间,与马克思主义一样,追问人类社会普遍规律。马克思主义则在工业文明时代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批判原子个体主义与西方现代性的异化,强调人的价值实现的社会历史过程,强调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样的人文理想,比自由主义更符合中华文化价值。在这里,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其现实性上是社会历史存在。离开社会性和历史性,就没有人的文化性。中华文化仿佛就是接受这个思想的天然温床。中华文化强调以文化人、学以成人,讲的就是人的社会化和历史化过程,将自然生命提升为道德生命,成为一个文化主体。在这里,人的道德生命实践是一个社会历史的文化过程,既是一个修齐治平过程,也是一个赞天地之化育过程。这种自强不息、奋斗不止的道德生命意识与文化主体精神,就与自由自觉创造历史、改造社会的历史唯物主义精神相贯通了。因此,早期共产党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很快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想主义与中华文化的道德理想主义融合起来,就不是偶然的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期重提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传统,倡导永久奋斗为第一政治道德,强调改造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完全符合中华文化的内在逻辑。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人文主义逐渐被国内知识界所熟悉。人们更加清晰地看到,马克思主义试图超越西方现代性的紧张关系,实现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实现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斗争的真正解决。但是,这样一种新人文主义,在西方文明内部缺乏土壤,而在中华文明中有其文化基因。中华人文精神,强调人与自然之间是一种天人合德的关系,人与人之间是同心同德的关系,强调民胞物与、一体同仁的关系。正是由于这两种人文精神的相通性,才可能理解中华文化主体性为什么可以通过马克思主义而激活,通过马克思主义而重建;正是由于这两种人文精神在长期的文化实践中已经有了融通的基础,我们今天才能提出“第二个结合”,并在党的创新理论中得到强有力的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但从当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整体实力来看,由于长期的学科壁垒、知识结构缺陷与学术包容度不够,知识界学贯中西、博通古今的思想性学术人才严重不足,学理阐释创新跟不上党的理论创新步伐,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还任重而道远。“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是我们党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打开了更加广阔的文化创新空间,必将打破学科壁垒与学术藩篱,坚持文化自信、开放包容、守正创新三原则,推动文化传承发展,进一步巩固和壮大中华文化主体性。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24年第7期 P4—P6
转载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2024-08-19 2024-08-21
一审:王凤梅 二审:何茂莉 三审:张清
编发:中国文化书院(阳明文化研究院)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 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