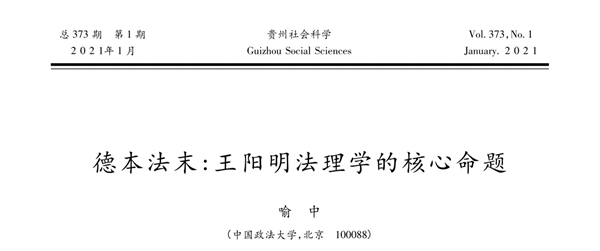
作者简介:喻中,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法理学。
基金项目: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儒家法哲学史研究”(17ZDA15)
摘要:王阳明立足于《大学》开篇规定的“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把德作为建构文明秩序、完善国家治理的主要依据。与此同时,王阳明也注意到“礼、乐、刑、政之法”对于治国理政的意义。德与法,就构成了二元并立的规范结构。就德与法之间的关系来看,根据王阳明关于“本”与“末”的二元划分,德是治国理政之“本”,亦即德治为本;法是治国理政之“末”,亦即法治为末。把德治为本与法治为末结合起来,就是“德本法末”。王阳明关于“德本法末”的构想,既渊源于古老的“明德慎罚”,同时也构成了当代中国强调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思想资源。
在中国法理学演进史上,王阳明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因为,王阳明在朱熹之后,对华夏文明秩序的建构方式进行了重新的思考,描绘了一幅从“明明德”开始、一直到“平天下”的路线图,从而促成了法理学在16世纪的更新。那么,如何描绘王阳明的法理学?尤其是,如何概括王阳明法理学的核心命题?显然,这是一个需要先行回答的问题。
太史公司马谈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有不省耳。”这就是说,先秦诸子的各种学说,都是“务为治”的学说,或者说,都是追求国家治理的学说。这可以说是华夏固有的学术思想传统。王阳明之学也在这个传统之中。同样,王阳明的法理学就像中国历史上先后兴起的法理学一样,也是围绕着“务为治”而展开的:以“治”为中心,建构规范体系,实现国家治理,优化文明秩序。其中,建构规范体系是方法,“治”则表征了目的。正如王阳明的历史分期理论所言:“唐、虞以上之治,后世不可复也,略之可也。三代以下之治,后世不可法也,削之可也。惟三代之治可行。然而世之论三代者,不明其本,而徒事其末,则亦不可复矣。”这句话很重要,为我们走进王阳明的法理世界,进而提炼王阳明法理学的核心命题,提供了关键性的线索:一方面,“三代之治”既代表了国家治理的理想方式,又代表了文明秩序的理想状态,因而是唯一可以效法的国家治理方式。另一方面,如果要效法“三代之治”,那就需要抓住两个要点:既要“事其末”,更要“明其本”。在王阳明看来,世人只知“事其末”,这是不行的;“事其末”虽然必不可少,但“明其本”显然居于更加重要的地位。
这就是说,“三代之治”有其“末”,更有其“本”;“三代之治”既是“末之治”,更是“本之治”。那么,王阳明所说的“本”与“末”又是什么?对于这样的问题,王阳明没有做出直接而明确的回答,但他有一个重要的提示,他说:“礼、乐、刑、政是治天下之法,固亦可谓之教,但不是子思本旨。”根据这个论断,第一,“礼、乐、刑、政”作为治理天下的“法”,虽然可以采用,但它并不是子思的“本旨”。如果它不是“本旨”,那它又是什么?在这里,根据“本”与“末”的两分法,不妨称之为“末旨”。第二,子思的“本旨”,就是孔子、曾子、子思、孟子所代表的儒家圣人的“本旨”,就是“本”。因而,所谓“本之治”,就是根据儒家圣人的“本旨”所展开的治理。第三,根据王阳明的《传习录》及《大学问》,子思及儒家圣人的“本旨”,可以归结为《大学》开篇所说的“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这其实就是仁政与德治。
由此可以推定,王阳明所说的“本”与“末”,主要指向“德”与“法”。这里的“德”,代表了从“明明德”到“亲民”再到“止于至善”这样一条线索,可以归属于“本”;这里的“法”,主要包括“礼、乐、刑、政”这样一些不能代表“子思本旨”的内容,可以归属于“末”。因此,“本之治”就是“德之治”,“末之治”就是“法之治”。推演至此,王阳明法理学的核心命题就可以概括为“德治为本,法治为末”,简而言之,就是“德本法末”。对于这个法理命题的意蕴,可以分述如下。
一、德治为本
要研究王阳明之学,最重要的文献是《传习录》;要研究王阳明的法理学,最重要的文献也是《传习录》。打开《传习录》,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亲民”与“新民”的辨析。这是《大学》首句提出的一个命题:“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里的“大学”是指“大人之学”,其实就是指儒家圣人之学。
按照《大学》,儒家圣人之学就在于“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关于其中的“亲民”,朱熹认为,应当解释为“新民”。但是,王阳明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说:“‘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与‘在新民’之‘新’不同,此岂足为据?”这句话见于《传习录》的开篇。从形式上看,讨论的是“亲民”与“新民”何者为优的问题,实质上却透露了王阳明关注的首要问题:明德。在王阳明看来,只有“亲民”两字,才符合“明明德”的旨趣。无论是“亲民”还是“止于至善”,都是“明明德”的延伸,朱熹以“新民”解释“亲民”,与“明明德”离得相对较远,因而显得“偏了”,“偏了”的见解其实就是偏见。
按照王阳明的“正见”,“大学之道”首先在于“明明德”,这既是古代圣人之见,其实也是王阳明本人反复申说的观点。根据《年谱》,王阳明在年仅11岁之时,曾经问过塾师:“何为第一等事?”塾师说:“惟读书登第耳。”王阳明的回应是:“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这就是王阳明早年结下的“圣胎”。这个“圣胎”既是理解王阳明之学的一把隐秘的钥匙,同时也是理解王阳明法理学的一把钥匙:王阳明有浓厚的“圣人情结”,也有“学圣贤”的自我期许。后来,王阳明确实也按照古代圣人之学,走出了一条从“明明德”到“亲民”再到“止于至善”的成德之路。这样的德性取向,透露了王阳明法理学的一个特质:这是一种具有浓厚道德色彩的法理学。
在此需要注意的是,“明明德”作为“大学之道”“大人之学”或“圣人之学”的一个纽结,绝不仅仅是现代意义上的、印刷在纸面上的“学术观点”。因为,古代的“圣人之学”也是“圣人之道”,既是圣人的理论学说,也是圣人的人生实践;按照王阳明的主张,既是知,也是行,具有知行合一的性质。而且,这里的“行”,既是圣人自己的修为,同时也是圣人治理天下的方案。“明明德”的法理意义由此显现出来:“明明德”就是把“明德”彰明、推广至普天之下,普天之下都将循“明德”而行,“明德”成为普天之下的人所遵循的规范——用今天的语言来说,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德治”。这样的“明明德”或“德治”是效法“三代之治”的根本,这就是“德治为本”。要全面理解王阳明的“德治为本”,有必要对他的德治观予以更细致的考察。
(一)德治以至善为目标
朱熹认为,应当到事上去寻求理,到事上去寻求善,王阳明则认为,对至善的追求,不必依赖各种外在的事物。因为,至善是心的本质属性。至善与“明德”具有相同的性质。如果把“明德”发展到圆满的程度,亦即“至精至一”的程度,那就是至善。这就是说,至善是升级版的“明德”。
对于这个观点,王阳明还有更进一步的阐述:一方面,无论是“至善”还是“明德”,都应当求之于“吾心”,都不必外求;如果到外物中去寻找,其结果将是:“生意支离决裂,错杂纷纭,而莫知有一定之向。”这句话既蕴含了对朱熹的批评,同时也正面阐明了向“吾心”寻求至善的理由:明德与至善都在“吾心”,那么寻求的方向就是确定无疑的,这样的方向不仅可以消除支离破碎的风险,而且还可以让“吾心”保守宁静的状态。而且,只有在宁静从容的状态下,“吾心”才可能做出精审的判断与取舍。这里的判断与取舍,既可以是个人的出或处,也可以是关于公共事务、治国理政的决断。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向“吾心”求善的法理意义:这样的求善方向,蕴含着国家治理、公共秩序建构等方面的指向——能够向内心寻求至善的圣人,才能够妥当地处理公共事务、安排公共生活、完善国家治理,从而满足一个政治共同体对于建构文明秩序的需要。
另一方面,“明德”通往“至善”,“至善”为“明德”提供了愿景。至善不仅是明德的极致,至善还是亲民的极致。至善是明德的本体,良知也是明德的本体,甚至天命之性也是明德的本体。这就是说,明德可以同时通往至善、良知、天命之性。后三者都是表征极致、极端、极则的概念,代表了明德能够达致的最终状态。这就是王阳明在《大学问》中旨在表达的治道与法理:明明德与亲民一定要止于至善。虽然,明明德、亲民已经设定了两条义务性规范:负有公共责任的士大夫应当履行明明德之义务与亲民之义务,但是,仅仅履行这两项义务还不够;在履行这两项义务的过程中,还必须抵达至善的程度。至善为明明德、亲民提供了一个可供追求的目标。
无论是明明德,还是亲民,都是以道德、德性为根本的政治:既是仁政,也是德治。但这样的德治必须追求至善这个目标,必须符合至善的要求,就像方圆要依“规矩”、长短要依“尺度”、轻重要依“权衡”。如果德治偏离了至善这个目标,就会出现三个方面的消极后果:其一,“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用其私智以揣摸测度于其外,以为事事物物各有定理也,是以昧其是非之则,支离决裂,人欲肆而天理亡,明德亲民之学遂大乱于天下。”其二,“固有欲明其明德者矣,然惟不知止于至善,而骛其私心于过高,是以失之虚罔空寂,而无有乎家国天下之施,则二氏之流是矣。”其三,“固有欲亲其民者矣,而惟不知止于至善,而溺其私心于卑琐,生意失之权谋智术,而无有乎仁爱恻坦之诚,则五伯功利之徒是矣。”
这三个方面的问题,代表了三种错误的立场。站在第一种立场上的代表人物是朱熹,他的问题是“支离”,他的“支离事业”把明德亲民之学搞乱了,导致是非准则、善恶标准趋于模糊。站在第二种立场上的人物主要是一些佛家、道家的信徒,他们也要明明德,但由于失去了至善这个目标,所以走向了空寂、出世,因而对于国家治理、天下治理没有助益。站在第三种立场上的代表人物,是那些私欲强烈的权术家,他们重功利、讲霸道、求霸术,他们即使有一些亲民的意愿,但没有追求至善的目标,因而只能在卑琐不堪的状态中徘徊,难以成就圣人之学与圣人之业。由此看来,王阳明对于佛家、道家、法家的立场,都是不能认同的,甚至与朱熹的立场也刻意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二)德治应当符合天理
德治应当追求至善这个目标,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只从“吾心”求至善,是否靠得住?这依然让人生疑。根据《传习录》,徐爱就有这样的疑惑,他的顾虑是:“至善只求诸心,恐于天下事理,有不能尽。”譬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间有许多理在,恐亦不可不察。”徐爱担心,一个人如果只是片面地求诸“吾心”,有可能不能很好地处理实际问题或具体问题,不能把事情办好、办成、办妥。譬如,事父、事君,特别是治理国家、治理天下,都需要遵循一定的规律,用现在的话来说,都是科学,都有专业性,都有技术含量。一个人如果只有“好心”,在实践过程中,完全可能“好心办坏事”,把事情“办砸”“搞糟”。当代中国曾经流行过“又红又专”的说法。让徐爱感到不安的问题也可以这样来理解:一个人如果“只红不专”,即使有追求至善之心,甚至已经达到至善的境界,恐怕也不能有效地解决实际问题。
徐爱的提问方式很平实,而且具有一定的现代色彩或专业意识。对于这样的疑问,王阳明回答说:“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从治道与法理的角度来看,事君、治民、平天下,只须在“此心”或“吾心”求天理,更具体地说,就是让“此心”成为“纯乎天理之心”,“纯乎天理之心”就是至善之心。如果至善是德治应当追求的目标,那么,天理同样就是德治应当符合的要求。
那么,此心如何达致“纯乎天理”的状态?答案很简单:一个人如果向往“大人之学”,他只需要袪除私欲。他不需要做加法,只需要做减法。袪除一分私欲,则增添一份天理。如果“此心”完全没有私欲,那就是“纯乎天理之心”。从“天理之心”的要求来看,德治的关键就是没有私欲。没有私欲,就会一心为他人着想。如果一心为父着想,那么,他对待父亲的方式自然就是孝;如果一心为君着想,那么,他对待君主的方式自然就是忠。推而广之,如果一心为国家、天下、民众着想,那么,他的治国理政,自然就会走向仁政与德治。
为了讲清楚这个道理,王阳明还举例加以说明:“就如讲求冬温,也只是要尽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间杂。只是讲求得此心。此心若无人欲,纯是天理,是个诚于孝亲的心,冬时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去求个温的道理;夏时自然思量父母的热,便自然要去求个清的道理。这都是那诚孝的心发出来的条件。”在家庭生活中,诚孝之心是根,是本,有了这个根本,冬天为父母御寒、夏天让父母清凉,就像从树干上长出的枝叶,自然就有了。对于治国理政来说,仁德之心是根,是本,有了这个根本,关心民间疾苦、促进公共利益,也像从树干上长出的枝叶,自然就有了。至于忠、孝的技术,以及治国理政的技术,不需要专门去学习,只要没有私欲之蔽,就可以做好。
如果不相信,那么,王阳明自己就是活生生的例子。按照他的“知行合一”之说,他既然深知“心即理”,深信“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于外就可以解决国家治理的问题,那么,我们可以推定,王阳明之心,确乎已经达到“纯乎天理”的状态。那么,他的“纯乎天理之心”是否长出了孝父、忠君、仁民之枝叶?是否长出了治理国家、平定天下之枝叶?纵观王阳明一生的事功,回答是肯定的。他多方征战,战无不胜;他多地临民,治绩突出,确实取得了非常好的实际效果,确实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王阳明的知与行确实是高度合一的。他的实践、事功是对他的观点的生动诠释。
但是,徐爱提出的问题依然是有意义的。王阳明既能够达致“纯乎天理之心”,还能够把“此心”发之于外,成就仁政与德治。但是,他的“知行合一”,其他人能否复制?其他人是否能够彻底袪除私欲、达致“纯乎天理之心”?更加重要的是,其他人即使可以做到这一步,他们能否依赖这样的“纯乎天理之心”做出“打仗无不胜”“治民无不成”的成就?或许是对这样的问题有所注意,或许是考虑到实际情况,或许是为了提升这个理论的普适性、可推广性。王阳明在强调袪私欲、存天理的同时,还提出了“在事上磨”的观点。据《传习录》上,陆澄提出的问题是:“静时亦觉工夫好,才遇事便不同,如何?”陆澄的意思是,碰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王阳明回答说:“是徒知静养,而不用克己工夫也。如此,临事便要倾倒。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
“在事上磨”之说,是要求在实践中增长才干,提升实际工作能力。此说可以看作是对前述徐爱之问的补充回答,相当于“打了一个补丁”,显得更接地气一些。当然,即使没有“在事上磨”一说,王阳明关于“纯乎天理之心”能够自然长出忠孝仁德之行的理论,也是可以成立的,因为,“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失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按照知与行之间的这种关系,如果你不能在社会实践中真正做到忠君、孝父、仁民,如果你不能实行仁政与德治,如果你实行的仁政与德治没有实现预期的效果,那就表明,你还没有达到真知的水平,你的“此心”也没有达致“纯乎天理之心”。因此,关键还是要让“此心”达致“纯乎天理之心”,这才是“根”,才是“本”。
(三)德治对良知的依赖
上文讨论“心即理”,这里的“即”字表明,心与理是一回事,心与理不能两分。有人问王阳明:“晦庵先生曰:‘人之所以为学者,心与理而已。’此语如何?”王阳明说:“心即性,性即理,下一‘与’字,恐未免为二,此在学者善视之。”心与理为什么不能分开来说?原因在于:心有一个重要的功能,那就是知,这样的“知”具有本体意义。德治根源于“吾心”,还需要追溯至“吾心”所具有的“知”这种本体。
知与心的关系是什么?王阳明解释说:“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由此看来,知是心的本体,也是心的本能,这样的本能一旦发动起来,就表现为良知。王阳明并未专门解释知与良知的关系。我们也许可以说,知就是良知,良知就是知。但是,王阳明的论述提到一个字,那就是“见”,这个“见”体现了知与良知的关系:本来,“知”作为心之本体,它可以是寂然不动的,可以是宁静安详的。然而,一旦“见”到了父,作为心的本体,知就自然表现出孝,当“吾心”“见父自然知孝”之际,知就呈现为良知。这就是说,由知转化成为良知,有一个必备的条件:出现了外在的事物(譬如,父、君、民,等等)。可见,知是心的本体,是一个本体性的概念,良知则主要体现为一个实践性的概念。
良知的实践性主要体现为决断。“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尔意念著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这就是说,良知就是决断,决断善恶,决断是非。只要你生起一个意念,只要你针对父、君、民,要想有所言行,这时候,良知的决断机制随之启动:它随即告诉你,你意念中的言行是善是恶。试想,如果良知充盈,仁就“不可胜用”,仁就可以获得丰厚的资源,仁政与德治随之获得了源源不竭的动力,这就是德治对良知的依赖。
上文还提到王阳明的一个判断:“知致则意诚”,此话该如何理解?在《答顾东桥书》中,顾东桥在来信中首先写到:“近时学者,务外遗内,博而寡要。故先生特倡‘诚意’一义,针砭膏肓,诚大惠也。”王阳明回答说:“吾子洞见时弊如此矣,亦将同以救之乎?然则鄙人之心,吾子固已一句道尽,复何言哉?复何言哉?若诚意之说,自是圣门教人用功第一义,但近世学者乃作第二义看,故稍与提掇紧要出来,非鄙人所能特倡也。”王阳明把“诚意”作为自己立说的根本,看作是“圣门教人用功”的第一义,并批评“近世学者”以“第二义”看待“诚意”——这里的“近世学者”依然是朱熹所代表的学者。所谓“第一义”“第二义”,依然还是“道问学”与“尊德性”之争。按照朱熹之学,要在事事物物上求天理,要走一条从“格物”到“致知”的成圣成德之路。正如朱熹在《大学章句》中所说:“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按照这样的顺序,格物是第一义,诚意是第二义。
但是,王阳明并不认同这样的路径。他在《大学问》之末段,专门论述了这个问题。一方面,他把“格物”解释为“去恶”,他说:“物者,事也,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谓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正其不正者,去恶之谓也。归于正者,为善之谓也。夫是之谓格。”这里的“为善去恶”,依然是对内的正心、诚意、致良知,并不是像朱熹所说的那样,在事事物物上去求个天理。另一方面,王阳明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作为一个事物来看待,他说:“格、致、诚、正、修者,是其条理所用之工夫,虽亦皆有其名,而其实只是一事。”具体到“格物”与“诚意”的关系来说,两者也“只是一事”。因为,心外无物,心物不二;同理,意外无物,意物不二。“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便是一物。意在于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于仁民爱物,即仁民爱物便是一物。意在于视听言动,即视听言动便是一物。所以某说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中庸言‘不诚无物’,大学‘明明德’之功,只是个诚意。诚意之功,只是个格物。”可见,诚意本身就是格物。
见于《答顾东桥书》及《大学问》中的这些话,清晰地展示了王阳明关于良知与德治关系的理解:德治依赖于“吾心”之良知。以朱熹为代表的“近世学者”,立足于从外在的事事物物上寻求天理,因而,“格”外在之“物”,是他们成圣成德的起点与基础。但是,王阳明认为,正心诚意才是成圣成德的起点与基础。所谓“格物”,并不是去研究外在的事物,而且,心外无物。如果没有“吾心”的关注与投射,哪有万事万物?因此,“格物”的真实含义是在内心实行“为善去恶”,狠斗“私”字一闪念。经过这种“为善去恶”意义上的“格物”,内心有善无恶,内心满是良知,内心没有私欲。把这样的良知运用于治国平天下,则国无不治,天下无不平。
以上三个方面表明,德治是至善、天理、良知的“道成肉身”。至善、天理、良知都是心的本体性存在,把这些本体性存在与国家治理结合起来,就是德治。由于至善、天理、良知在王阳明之学中,居于根本的地位,德治作为至善、天理、良知凝聚而成的肉身,在国家治理体系中,也居于根本性的地位,这就是德治为本。
二、法治为末
与“德治为本”相对应的,是“法治为末”。这里的本与末,如上文所述,是王阳明使用的一种修辞,本是指树根、树干,末是指树枝、树叶。在王阳明建构的国家治理体系中,一方面,德治为本,对此上文已有阐述;另一方面,法治为末。当然,王阳明并没有直接提出“法治”这个概念,但他讨论了“礼、乐、刑、政之法”对于国家治理的意义。根据“礼、乐、刑、政之法”完善国家治理,把“礼、乐、刑、政之法”作为治国理政的规则,这样的治道,可以概括为法治。
王阳明关于“法治为末”的主张,见于1518年他写给薛侃的一封信中。他借此信告诉薛侃:“即日已抵龙南,明日入巢,四路皆如期并进,贼有必破之势矣。向在横水,尝寄书仕德云:‘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区区剪除鼠窃,何足为异?若诸贤扫荡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诚大丈夫不世之伟绩。”在“兵刑同义”的固有传统中,“破山中贼”,主要是以“兵刑”治国平天下,这样的事业,在王阳明看来,过于平常,并不会增添自己的荣耀。相比之下,“破心中贼”,才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伟业。两种事业在王阳明设定的价值体系中高下悬殊,足以表明,相对于德治这个根本,法治确实处于“末”的地位。
王阳明的治理实践也可以体现出“法治为末”的倾向。根据《年谱》,1518年4月,“先生谓民风不善,由于教化未明。今幸盗贼稍平,民困渐息,一应移风易俗之事,虽未能尽举,姑且就其浅近易行者,开导训诲。即行告谕,发南、赣所属各县父老子弟,互相戒勉,兴立社学,延师教子,歌诗习礼。出入街衢,官长至,俱叉手拱立。先生或赞赏训诱之。久之,市民亦知冠服,朝夕歌声达于委巷,雍雍然渐成礼让之俗矣。”在南赣地区,“礼让之俗”的形成,表明社会治理已经取得了良好的绩效。然而,这种治理绩效的取得,主要是“开导训诲”“歌诗习礼”的产物,亦即“德治”的产物,并非“法治”的产物。
稍作追溯还可以发现,这种德治为本、法治为末的构想,在王阳明主政地方的初期就已经显现出来。早在1510年,38岁的王阳明就任庐陵县知县,这是王阳明离开贵州之后,首次主持一县政务。在庐陵的治理实践中,一方面,他不事威刑,不依赖刑法的威慑作用。另一方面,他尽可能开导人心,并以之为本。这样的为政之道,即为德治为本、法治为末。
尽管相对于“为本”的德治,法治处于“为末”的地位,但是,在治理实践中,王阳明对法治还是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因为法治也是必不可少的。根据王阳明的“礼、乐、刑、政之法”一语,他的法治世界可以分为“礼乐之治”与“政刑之治”来分别考察。
(一)礼乐之治
礼乐之治,主要是礼之治。在“礼、乐、刑、政”这四种“法”规范中,礼的地位也是首屈一指的。如何发挥礼在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作为法治的一个组成部分的礼治,应当如何展开?如何把握礼治的基本原则?显然就是一些关键性的问题。
根据《寄邹谦之·二》,邹谦之在来信中提出了一个具体的问题:根据朱熹制定的家礼,祭祀祖宗时应当由西向东摆放历代祖宗的灵位,但是,这种祭礼让人觉得不安。王阳明的回答是:“古者庙门皆南向,主皆东向。合祭之时,昭之迁主列于牖,穆之迁主列于南牖,皆统于太祖东向之尊。是故西上,以次而东。今祠堂之制既异于古,而又无太祖东向之统,则西上之说诚有所未安。”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是:“礼以时为大,若事死如事生,则宜以高祖南向,而曾、祖、祢东西分列,席皆稍降而弗正对,似于人心为安。”祭祀过程中祖宗牌位的摆放,是一个非常具体的祭礼,见于《文公家礼》中的相关规定让邹谦之感觉不安,王阳明对此提出了相应的修改建议,实际上是修改了朱熹制定的家礼。与此同时,王阳明还提出了一个原则性的观点:“礼以时为大”。
所谓“礼以时为大”,就是要根据时代的变化,对礼的内容进行适当的修改,使之满足时代的需要。还是在《寄邹谦之·二》中,王阳明比较全面地表达了关于礼治的基本思想。一方面,关于礼的规则,亦即礼法,并非越古越好。古礼并不是后人崇拜的对象,更不是后人迷信的对象。如果只是在形式上遵循古代的礼法,如果古礼不能让人心安,那样的礼,甚至可以称为“非礼之礼”。所谓“非礼之礼”,是指不符合礼的本质要求的礼,这就相当于“非法之法”,是指不符合法的基本要求的法。譬如,显示失正的法,以不合法的程序制定出来的法,都可以归属于“非法之法”。王阳明提出的“非礼之礼”也是这种情况:如果它“不得于心”,那就不符合礼的要求。这样的礼,即使载之于古籍,也不必拘泥。另一方面,礼是根据人情而制作的符节、文字,礼的依据是人之常情,这是礼能够长期发挥作用的根源。如果一个时代的风气、习俗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礼也将随之发生变化。如果我们不能理解某种古代的礼,那主要是因为时代发生了变化。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看,沿着那些难以理解的古礼进行索解,可以开启一个相异的历史世界与意义世界,可以还原、再现一个旧时代的风气、习惯。当然,从法理学研究的角度来看,那就要立足于运动变化的观点,进而看到,没有永恒不变的礼,只有随着时代变化的礼。
还有一个方面,那就是关于礼的“简易之说”,其基本旨趣在于:促使礼向易知易行的方向变化。这样的“简易之说”,其实反映了王阳明一贯的立场。从思想渊源上,“简易之说”由来已久,《易传·系辞上传》已有这样的表达:“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南宋的陆九渊作为王阳明之学的前驱,早已在题为《鹅湖和教授兄韵》的诗中主张:“易简功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辨只今。”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王阳明又作了新的发挥。据《传习录》:“王汝中、省曾侍坐。先生握扇命曰:‘你们用扇。’省曾起对曰:‘不敢。’先生曰:‘圣人之学不是这等捆缚苦楚的。不是装做道学的模样。’”这个典故,生动地表现了王阳明不重形式、简易为礼的思想倾向。
更全面地看,王阳明关于礼治的观点,都可以在反对“虚文”、强调“实行”的思想框架下来理解。“礼以时为大”就是要强调礼与时代的契合,让礼的规则符合时代、人情、人心的需要,从而更好地发挥礼在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中的功能。
在礼乐之治中,礼之治是重心,乐之治也有必要予以一定的注意。关于“乐之治”,王阳明有一个观点:“古乐不作久矣,今之戏子,尚与古乐意思相近。”看到戏子与古乐的相通之处,主张充分发挥戏子的作用,让戏子助成“乐之治”,也可以反映王阳明强调“实行”的精神与风格。
(二)政刑之治
与“礼乐之治”相伴随的,还有“政刑之治”。由于王阳明有主政地方与带兵打仗的经历,因而在“政刑之治”方面,也有知行合一的成就。就像“礼乐之治”可以分为“礼之治”与“乐之治”一样,“政刑之治”也可以分为“政之治”与“刑之治”。
先看“政之治”。王阳明在为政或关于“政之治”的探索过程中,一个比较突出的创新是“十家牌法”。这可以视为王阳明为了推进地方治理而制定的一项法律制度。在《十家牌法告谕各府父老子弟》一文中,王阳明解释了创制这项法律制度的意图:这是在尊重乡民与治理乡民之间进行权衡的结果。一方面,对于乡民中众多的诗书礼义之家,本来应当予以足够的尊重,但是,另一方面,既然乡民中那些作奸犯科者已经对国家治理、地方治理构成了明显的危害,为了清除这样一些危害,还得创立并实施“十家牌法”,因此,这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
“十家牌法”的具体内容,首先是把十户人家作为一个单元来管理。每家的人口状况如实登记。每家人口多少,每个人的职业是什么,每个人的年龄状况、身体特征,以及户籍、田产等等,全部登记造册,上报政府。政府如果要征调民力,或者要实施其他方面的常规管理,都可以根据这个册子载明的信息。由此看来,“十家牌法”首先是要建立一个“数据库”,有了这个“数据库”,就可以进行精细化的治理。其次,“十家牌法”以十家为单元,上报十家范围内有不良行为甚至是有恶行的人,这些人的名单由政府掌握,如果这些人能够改恶从善,政府可以不再追究,但是,必须由十家共同担保。这项措施,其实是在十家范围内,形成一个惩恶扬善的共同体,十家范围内的这个群体,共同充当了惩恶扬善的责任共同体。以现在的理论与实践来说,这一措施既促成了治理重心的下移,同时也节省了政府的治理成本,可以理解为政府指导下的“十家自治”。再次,如果十家之内出现了盗窃等方面的违法犯罪行为,十家作为一个单元,可以组织起来缉拿违法犯罪者。在这种情况下,“十家”又承担了刑事侦查的职能。最后,十家作为一个单元,还承担了处理纠纷的职能。如果出现了纠纷,“十家”要想办法化解纠纷;即使没有出现纠纷,十家之内,也要相互提醒,时刻讲信修睦,预防可能出现的纠纷。
对于“十家牌法”在实践中的功能与作用,王阳明是很有信心的。通过“十家牌法”,为什么可以取得很好的治理绩效?根本的原因在于:十家牌法是一种推进基层自治的制度安排。作为国家或政府,虽然可以“不劳”而治,但是,十家范围内的民众,其实付出了相应的劳动:他们相互劝解、相互提醒、相互监督。由此可见,“十家牌法”实际上是一种发动民众、动员民众实现基层治理之法。
王阳明推动基层自治,既有“十家牌法”,还有“乡约”这种制度安排。王阳明推行的“乡约”与当代中国的乡规民约或村规民约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是,当代的乡规民约通常是乡民自己创制的,而王阳明推行的“乡约”却是出于王阳明的创制。在这个方面,王阳明创制的《南赣乡约》颇有代表性。从内容上看,《南赣乡约》就相当于王阳明为南赣地区的民众制定的一部“基本法”。这部“南赣基本法”就像现代的宪法一样,既有序言,也有正文。正文是南赣民众应当普遍遵循的行为规范。序言就像现代的宪法序言一样,主要交待创制乡约的整体背景,同时也明确宣告创制这个乡约的价值目标:惩恶扬善、讲信修睦、敦风厉俗,如果能促使“南赣之治”走向“三代之治”,那就再好不过了。关于这部乡约的序言与正文,这里不再详细述评。然而,如果把这部《南赣乡约》与“十家牌法”结合起来,就可以看到,《南赣乡约》实为“十家牌法”的延伸。
“十家牌法”与《南赣乡约》大致可以代表王阳明的“为政之法”。为了保障这样的法能够得到严格有效的实施,还需要另一种“法”——它可以作为一种保障性的、强制性的后盾,那就是刑。倘若要与“为政之法”形成某种对应,那么,这种保障性的“刑”也可以理解为“为刑之法”。尽管在“礼、乐、刑、政之法”这个范围内,王阳明对“刑”的论述相对较少,但它却是不可或缺的。
早在弘治十二年,亦即1499年,针对当时的边陲之患,年仅27岁的王阳明就向朝廷提交了一份“决策咨询报告”,这就是留传至今的《陈言边务疏》。在这份报告中,王阳明提出了八项政策建议,其中就包括“行法以振威”,这项政策建议的背景是:当时的边臣即使损兵折将,也不会受到惩罚。东边的将领打了败仗,就调到西边继续为将。由于君主对败军之将并不加罪,所以各地的边臣并不把打败仗当回事。王阳明提出,如果能够把那些败军之将按照军法斩于辕门,“行法以振威”,同时,把那些来自权门的“总兵官”从军队系统中全部剥离出来,那么,边务问题就会得到有效的解决。
治理边患需要“行法以振威”,治理内患同样需要“行法以振威”。在《申明赏罚以厉人心疏》中,王阳明要求以严格、及时的赏罚以提振军威。在王阳明看来,关于赏罚之法,朝廷并不是没有规定,只是没有明确地予以公布,更没有严格地实施。如果不及时公布、不及时实施这样的法,那么,国家的军队在敌人面前,就会退缩不前,将领无以激励军队,内乱就难以平息。
王阳明认为,无论是治理内乱还是治理外患,都需要运用刑法以提振军威。不过,王阳明毕竟还是更加看重《大学》中的“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因此,即使在强调“行法以振威”之际,也没有忘记德治为本。正如《绥柔流贼》篇所说:“夫善者益知所劝,则助恶者日衰;恶者益知所惩,则向善者益众;此抚柔之道,而非专有恃于兵甲者也。”立足于去恶扬善,还需要注意:“刑赏之用当,而后善有所劝,恶有所惩;劝惩之道明,而后政得其安。”因为刑赏的最终目的,还是在于对善的追求,而且最终还要“止于至善”,毕竟这才是根本。有鉴于此,“君子之政,不必专于法,要在宜于人;君子之教,不必泥于古,要在入于善。”君子为政,“刑之治”虽然是必不可少的,但绝不能仅仅依赖于“刑”,最终的决定性因素还是在于人,所谓“人”,其实就是人的德性。
概而言之,国家治理离不开“礼、乐、刑、政之法”,但从更宽的视野中看,特别是从文明秩序的安顿来说,“礼、乐、刑、政之法”毕竟还只是“末”。只有追求止善的德治,才是治国理政之“本”。这就是王阳明面向治国理政所建构的“德本法末”,它作为王阳明法理学的核心命题,反映了王阳明完善国家治理、建构文明秩序的基本构想。
三、德本法末的源与流
上文分德治与法治两个方面,阐述了王阳明关于德本法末的构想。在此基础上,还有必要从思想史的角度,考察王阳明“德本法末”的源与流。有必要以王阳明为中轴,从源与流两个方向,察看王阳明德本法末命题的由来,以及这一命题对后世的影响。
(一)从“有德无法”到“德本法末”
在传统中国,在大多数情况下,“法”“刑”“律”都可以互训。因此,传统中国的德法关系也可以表述为德与刑的关系,或者是德与律的关系。
在中国思想史上,关于德与法的关系的思考,几乎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古老。《吕氏春秋·上德》在追溯中国的早期历史时认定:“为天下及国,莫如以德,莫如行义。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劝,不罚而邪止。此神农、黄帝之政也。”这就是说,早在神农、黄帝时代,治理国家的关键主要就是一个德与罚的关系问题。只是,在德与罚之间,实行德政、推行德治居于主导地位,甚至是唯一的选择与方向。在那个时代,厉行德治,就实现了对国家及天下的有效治理。至于通过法律实施的奖励与惩罚,完全可以置而不用。神农、黄帝时代的德法关系,可以概括为“有德无法”。不过,按照前文征引的王阳明的论述,神农、黄帝时代的国家治理可以归属于“唐、虞以上之治,后世不可复也,略之可也”,这种“有德无法”的结构,尽管可以“略之”,但也可以代表华夏文明初创时期德法关系的一种萌芽。
按照王阳明的历史分期理论,紧接着“唐、虞以上之治”的,是“三代之治”,正是在“三代”时期,出现了关于德法关系的一种新形态,那就是周公阐述的“明德慎罚”。根据《尚书·康诰》,周公对康叔提出的要求是:“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在周公看来,这种明德慎罚的实践早在商代就已经形成了。正如周公在《尚书·多方》中所指出的:“乃惟成汤克以尔多方简,代夏作民主。慎厥丽,乃劝,厥民刑,用劝。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罚,亦克用劝。”这就是“三代”盛行的明德慎罚。这是王阳明奉为圭臬的关于德法关系的一种经典模式。
德法关系的第三种模式,可以概括为德主刑辅。根据《论语·为政》,孔子关于国家治理有一个著名的论断:“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个论断把“德礼”与“政刑”进行了划分,并在德礼与政刑之间,进行了等级化的处理,可以视为德主刑辅关系模式的一个雏形。以孔子的论断为基础,汉代的董仲舒对于德与法的关系,进行了更具体的思考,他说:“圣王之治天下也,少则习之学,长则材诸位,爵禄以养其德,刑罚以威其恶,故民晓于礼谊而耻犯其上。”立足于阴阳理论,董仲舒又认为,“天以阴为权,以阳为经。阳出而南,阴出而北。经用于盛,权用于末。以此见天之显经隐权,前德而后刑也。故曰:阳,天之德;阴,天之刑也。”这些关于“德前刑后”或“德阳刑阴”的论述,可以作为“德主刑辅”的一种替代性表达方式。到了唐代,《唐律疏议·名例》比较正式地确认了一个基本原则:“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这个原则可以简化为“德本刑用”,按照传统中国的“体用论”,也可以解释为:德为体、刑为用,或“德体刑用”。
到了宋代,朱熹在注释孔子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一句时写道:“愚谓政者,为治之具。刑者,辅治之法。德礼则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礼之本也。此其相为终始,虽不可以偏废,然政刑能使民远罪而已,德礼之效,则有以使民日迁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当深探其本也。”朱熹关于德、礼、政、刑的排序意味着,在国家治理体系中,这四个元素重要性依次递减。朱熹明确指出了德为礼之本,但大致可以推断,礼也可以作为政之本,政也可以作为刑之本。根据这样一个链条,德与法的关系,大致可以概括为“德本刑辅”或“德主刑辅”。
归纳以上各家观点,神农、黄帝时期盛行“有德无法”的实践。从周公、孔子、董仲舒,一直到朱熹,都对德法关系进行了界定。在不同时代的各种论述中,包含了一个共同的特点:都主张重德而轻法,都认为德与法不能等量齐观。从相异的方面来看,各种论述各有侧重:周公要求彰明德治、慎用刑罚。孔子认为德治具有伦理意义,但政刑之治却没有伦理意义。董仲舒以尊卑关系、阴阳关系定性德法关系。朱熹描述德法关系的关键词是“本”与“辅”。
正是在这样的传统中,王阳明对德法关系进行了重新的建构,那就是德为本、法为末。与朱熹之前的各家学说一样,王阳明也彰显了德的重要性。这就是说,朱熹之前的各家学说,构成了王阳明“德本法末”理论的源头。但是,王阳明对于德法关系理论也有所创新。在王阳明看来,德相当于树根、树干,法相当于树枝、树叶。法是德派生出来的,法对德具有直接而明显的依附关系。而且,法本身不具有独立性,如果没有德,法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末。王阳明如此界定德与法的关系,一个根本的原因,在于他的心性本体论:万物唯心,万事唯心,心外无物,心外无事。仁与德都是心性的外化,因而构成了国家治理所依据的根与本。因而,从思想渊源上看,王阳明的“德本法末”是传统中国由来已久的德法关系理论与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相结合的产物。
(二)从“德本法末”到“法德结合”
在王阳明身后,王阳明之学引起了广泛的回响,不仅在中国,而且在韩国、日本,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来者从不同的角度,对王阳明之学进行了不同的评析。但是,相对说来,在众多的“王学”研究文献中,关于“德末法末”及相关问题的讨论,还是比较少见的。主要的原因在于,从法理学的角度研究王学的成果较少;从哲学或思想史的角度研究王学的学者,又很难注意到他关于“礼、乐、刑、政之法”的思想。然而,如果我们从国家治理、文明秩序建构的层面切入,从法理学的角度关注王阳明之学,就可以看到,王阳明关于德本法末的构想,对现代中国具有明显的塑造作用。
先看今日流行的孙中山的《建国方略》一书,此书由三篇文献组成,其中第一篇为《孙文学说——行易知难(心理建设)》,这篇文章初次发表于1919年。由这篇文章的标题即可看到,孙中山自命的“孙文学说”,几乎就是对王阳明心学的一种创造性的发挥。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主张知行不二。孙中山也讲知行关系,只是在知与行的关系上,把“知”置于更加关键的位置,亦即把“心理建设”置于更加关键的位置。1918年12月31日,孙中山在《建国方略》所写的自序中说:“夫国者人之积也,人者心之器也,而国事者,一人群心理之现象也。是故政治之隆污,系乎人心之振靡。吾心信其可行,则移山填海之难,终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则反掌折枝之易,亦无收效之期也。心之为用大矣哉!夫心也者,万事之本源也。”由此可见,孙中山的建国方略,首先是心理建设。这种以心为万事本源的思想,与王阳明的“心外无事”具有很大的共通性。
孙中山在这篇自序中提到了“移山填海之难”,特别是其中的“移山”这个意象,在毛泽东1945年写成的《愚公移山》这篇名文中,又有专门的论述。
按照孙中山的论述,尤其是按照毛泽东的这篇名文,只要有“移山之心”,就可以做出“移山之行”,就可以完成“移山之事”。这都是没有问题的。在孙中山的《孙文学说——行易知难(心理建设)》与毛泽东的《愚公移山》之外,还有一篇值得注意的文献,那就是毛泽东在1939年写成的《纪念白求恩》,毛泽东在此文中称赞白求恩:“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毛泽东的这些话,以及毛泽东的这篇文章,还有《愚公移山》及《为人民服务》,尤其是由此组合而成的“老三篇”,对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革命,以及对20世纪中叶以后的国家治理,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毛泽东写下的这些文献,与孙中山的“孙文学说”一样,都强调了无私的德性对于政治共同体的凝聚、文明秩序的建构、国家治理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这样的观点,与王阳明“德本法末”中的“德本”,具有遥相呼应的关系。“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在相当程度上,就像是一个“止于至善”的人,他具有“纯乎天理之心”,“若良知之发,更无私意障碍。”
“老三篇”都强调“无私”这样的德性。这样的思想、观点不仅仅是毛泽东一个人的,而是代表了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共识。譬如,同样是在1939年完成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中,刘少奇专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共产党员应当如何提升自己的修养呢?刘少奇以孔子与孟子为例,要求共产党员“必须注意在革命斗争中的锻炼和修养。”[18]刘少奇的这篇论述,从孔子、孟子的修身开始讲起,一直讲到共产党员的修养,其核心就是要袪除私欲之蔽,提升共产主义之德。
从孙中山到毛泽东、刘少奇的论述中,都可以看到王阳明之学在现代中国的延伸。王阳明没有直接提出“德本法末”这样一个命题,他关于“明德”“亲民”“至善”的论述,与他关于“礼、乐、刑、政之法”论述是分别展开的,但是,我们可以根据他反复提到的“本”与“末”,把他关于国家治理的法理构想概括为“德本法末”。同样,现代的孙中山、毛泽东、刘少奇也没有直接提出“德本法末”这样一个命题。但是,把他们的思想理论与政治实践加以融会贯通,就可以发现,他们都强调了心理建设、道德修养对于革命、建国、治理的根本意义,这跟王阳明的“德本”观念具有一定的源流关系。
不过,以上引证的孙中山、毛泽东、刘少奇的论述,都是在20世纪上半叶形成的,其中,孙中山的“孙文学说”从诞生至今,已经超过了一百年。百年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与思想文化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的背景下,重新思考王阳明的“德本法末”,就会发现,德与法的关系不仅存在,而且极具现实意义。
在当下的中国,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时代,法治的价值受到了普遍的推崇,没有人会反对法治,也没有人轻视法治,更不会把法或法治看成是细枝末节。如果有人像王阳明那样,用“本与末”这一对范畴来宣扬其法理学说,一定会招致普遍的反对。然而,即使是在这样的思想、理论、学术背景下,当代中国也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在这里,德治与法治是“相结合”的关系,而且法治排在了德治之前,这样的德法关系或可概括为“法德结合论”。这样的德法关系或法德关系,是对当代中国国家治理需要的回应,已经不是王阳明的“德本法末论”所能够解释的了。不过,德与法的关系依然存在。在国家治理体系中,以德治国依然不可或缺。这就意味着,王阳明的“德本法末”构想在现代及未来中国,依然具有潜在而深远的意义。即使着眼于思想史的层面,从当代中国的“法德结合”回溯到王阳明的“德本法末”,亦有助于理解“法德结合”蜿蜒而来的历史轨道。
图文收集与编发:中国文化书院(阳明文化研究院)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 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