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论《阳明先生年谱》嘉靖本与全书本的差异
2021年第2期《现代哲学》刊载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副教授邓国元、贵州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硕士生王大印贵州省国学单列项目“阳明学‘四句教’与中晚明理学发展衍化研究”(19G2GX32)成果,题:王阳明“临终遗言”献疑与辨证——兼论《阳明先生年谱》嘉靖本与全书本的差异。全文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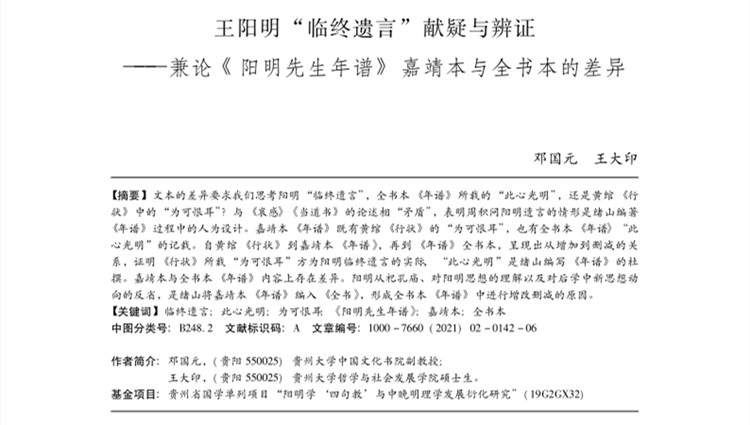
摘要:文本的差异要求我们思考阳明临终遗言,全书本《年谱》所载的此心光明,还是黄绾《行状》中的为可恨耳?与《哀感》《当道书》的论述相矛盾,表明周积问阳明遗言的情形是绪山编著《年谱》过程中的人为设计。嘉靖本《年谱》既有黄绾《行状》的为可恨耳,也有全书本《年谱》此心光明的记载。自黄绾《行状》到嘉靖本《年谱》,再到《年谱》全书本,呈现出从增加到删减的关系,证明《行状》所载为可恨耳方为阳明临终遗言的实际,此心光明是绪山编写《年谱》的杜撰。嘉靖本与全书本《年谱》内容上存在差异。阳明从祀孔庙、对阳明思想的理解以及对后学中新思想动向的反省,是绪山将嘉靖本《年谱》编入《全书》,形成全书本《年谱》中进行增改删减的原因。
关键词:临终遗言;此心光明;为可恨耳;《阳明先生年谱》;嘉靖本;全书本;
基金项目:贵州省国学单列项目“阳明学‘四句教’与中晚明理学发展衍化研究”(19G2GX32);
在王阳明(1472-1529)生命历程中,记载于《王文成公全书》1 (下文简称《全书》)卷34《阳明先生年谱》2 (下文简称《年谱》)的“临终遗言”“此心光明,亦复何言”,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这不仅是研究阳明生平的要点,甚至成为阳明思想世界和人格精神的象征。然细考相关文献可以发现,阳明临终遗言存在不同的记载,特别是黄绾(1480-1554)在《阳明先生行状》(下文简称《行状》)中记述的“他无所念,平生学问方才见得数分,未能与吾党共成之,为可恨耳”,与全书本《年谱》所载内容存在显著差异。这种文本的差异表明,在考察阳明临终遗言时需要作仔细分辨与讨论。同时,嘉靖本《年谱》与全书本《年谱》、黄绾《行状》在相关内容的记载上皆有异同,个中情况也值得认真分析,这是研究阳明临终遗言问题的关键。本文以相关文献和学界已有研究为基础,对阳明临终遗言提出献疑与辨证,以呈现阳明临终遗言的本来实际。鉴于阳明临终遗言涉及嘉靖本与全书本《年谱》内容上的差异问题,本文也拟对两种《年谱》略作文献上的比较考察。
一
关于王阳明生平及思想历程载于《全书》卷32-34,由钱德洪(1496-1574)主要负责编撰的《年谱》无疑是最主要的文献和依据。在阳明人生历程中,最后时刻的临终遗言是其中的关键内容。全书本《年谱》嘉靖七年戊子(1528)“十一月丁卯,先生卒于南安”条下载:
是月廿五日,逾梅嶺至南安。登舟时,南安推官门人周积来见……遂问道体无恙。先生曰:“病势危亟,所未死者,元气耳。”积退而迎医诊药。廿八日晚泊,问:“何地?”侍者曰:“青龙铺。”明日,先生召积入。久之,开目视曰:“吾去矣!”积泣下,问:“何遗言?”先生微哂曰:“此心光明,亦复何言?”顷之,瞑目而逝,二十九日辰时也。3
就阳明临终遗言而言,此处记载涉及两个要点:其一,阳明临终遗言的具体内容为“此心光明,亦复何言”;其二,阳明临终遗言的见证人是南安推官门人周积(1483-1565)4。这里“此心光明,亦复何言”的临终遗言,不仅成为阳明生命历程的重要节点,也可谓其人格精神与思想境界的标志。不过,黄绾在《行状》中针对阳明临终遗言有不同记载,也引出了问题:
十月初十日,复上疏乞骸骨,就医养病……至大庾嶺,谓布政使王公大用曰:“尔知孔明之所以付托姜维乎?”大用遂领兵拥护,为敦匠事。廿九日至南康县,将属纩,家童问何所嘱。公曰:“他无所念,平生学问方才见得数分,未能与吾党共成之,为可恨耳!”遂逝。5
黄绾《行状》此处文字同样涉及两个关键内容:其一,阳明最后遗言的内容为“他无所念,平生学问方才见得数分,未能与吾党共成之,为可恨耳”;其二,阳明临终遗言的见证人是其家童。显然,相较于全书本《年谱》的“此心光明,亦复何言”,《行状》中“他无所念,平生学问方才见得数分,未能与吾党共成之,为可恨耳”的记载,不仅存有差异,甚至可以说相反,前者为“无憾”,后者则是“有恨”。同时,阳明临终遗言的见证人从门人周积变成家童,也可谓截然不同。全书本《年谱》与黄绾《行状》所载文本的差异促使我们思考:阳明临终遗言当如黄绾《行状》所载,还是如全书本《年谱》所载?阳明临终遗言的见证人是门人周积,还是家童?6
依据文献产生时间先后,先对黄绾《行状》作讨论。按照湛若水(1466-1560)在《阳明先生墓志铭》(下文简称《墓志铭》)中“甘泉子挈家闭关于西樵山烟霞之洞,故友新建伯阳明王先生之子正亿以其岳舅礼部尚书久庵黄公之状及书来请墓志铭”7的论述可知,黄绾写就《行状》后,曾安排阳明之子正亿(1526-1577)携《行状》和书信拜访甘泉,并向甘泉求作《墓志铭》。而据《墓志铭》中“久庵公为之状,六年而后就,慎重也”8的内容,可知黄绾《行状》完成于阳明逝世6年后,即嘉靖十三年(1534)。无论是就黄绾与阳明之间特别的“亦师亦友亦亲家”9关系,还是就《行状》在阳明生平传记文献时间上的早出,以及从甘泉所说之“慎重”来看,足以说明《行状》是“后世学者了解、洞悉王阳明生平事迹最可靠、最权威的文本之一”10。这也表明在考察阳明临终遗言时,需要重视和肯定《行状》所载文本的可靠性、权威性。
再来讨论全书本《年谱》所载的文献。单就全书本《年谱》所载周积为阳明生命最后时刻见证者这一方面,作为《年谱》主要编撰者的钱绪山,在其他文献中有着不同论述,呈现了不同信息。阳明逝世后,绪山曾作《遇丧于贵溪书哀感》(下文简称《哀感》),其中有记云:
嘉靖戊子八月,夫子既定思、田、宾、浔之乱,疾作……二十一日逾大庾嶺,方伯王君大用密遣人备棺后载。二十九日疾将革,问侍者曰:“至南康几何?”对曰:“距三邮。”曰:“恐不及矣。”侍者曰:“王方伯以寿木随,弗敢告。”夫子时尚衣冠倚童子危坐,乃张目曰:“渠能是念邪!”须臾气息,次南安之青田,实十一月二十九日丁卯午时也。是日,赣州兵备张君思聪,太守王君世芳,节推陆君府奔自赣,节推周君积奔自南安,皆弗及诀,哭之恸。11
绪山于《哀感》中也论及阳明生命最后情形。较之黄绾《行状》和全书本《年谱》,《哀感》并没有记载阳明临终遗言的具体内容,但与全书本《年谱》所载相同的是,《哀感》也提到周积。值得注意的是,《哀感》虽论及到周积,但明确指出周积“奔自南安”而“弗及诀”,即没有见到阳明最后一面。这与全书本《年谱》中周积为阳明临终遗言见证人的论述不一致,存在明显“矛盾”。鉴于《哀感》作于阳明逝世6年(1534)后12,《年谱》作于阳明逝世35年(1563)后的情况,显然前者的记载当更接近实际情况。同时,基于《哀感》中周积等人没有见到阳明最后一面的事实,阳明最后时刻的见证人就不可能是其门人,而更应该是“夫子时尚衣冠倚童子危坐”中的童子。另外,绪山在《谢江广诸当道书》(下文简称《当道书》)中透露的信息与这里的讨论也直接相关:
冬暮,宽、畿渡钱塘,将趋北上。适广中有人至,报父师阳明先生以病告,沿途待命,将逾庾嶺矣。即具舟南迎,至兰溪,忽闻南安之变。慌怖三问三疑,奔至龙游,传果实矣……在吾师以身许国,死复何憾,独不肖二三子哀恨之私,有不能一日解诸怀耳。夫子讲学四十余年,从之游者遍海内,没乃无一人亲含襚,殓手足,以供二三子之职,哀悯何甚!13
细节内容暂且不论,单从绪山此处“夫子讲学四十余年,从之游者遍海内,没乃无一人亲含襚,殓手足,以供二三子之职,哀悯何甚”,特别是“没乃无一人亲含襚,殓手足”的记述来看,充分表明阳明逝世时没有弟子在身边的事实。这不仅与《哀感》中周积等去见阳明最后一面“皆弗及诀”的记载相一致,更足以说明全书本《年谱》所谓周积问阳明“何遗言”的内容,完全可能是后来绪山在编写《年谱》过程中的杜撰14。合而观之,就阳明生命最后时刻的见证者而言,《哀感》中“夫子时尚衣冠倚童子危坐”,周积等人来见阳明最后一面“皆弗能诀”,以及《当道书》中“无一人亲含襚,殓手足”的记述,无疑与黄绾《行状》中家童问阳明“何所嘱”的内容相一致。这更证明阳明临终情形当如黄绾《行状》所载,实为“家童问”是也。进而不难得出结论:阳明临终遗言的具体内容当如黄绾《行状》所载,是“他无所念,平生学问方才见得数分,未能与吾党共成之,为可恨耳”,而非全书本《年谱》所载的“此心光明,亦复何言”。不过,在明确得出此结论之前,需要围绕全书本《年谱》中“此心光明,亦复何言”的记述作进一步考察,以呈现其产生的过程与原由。
二
由绪山负责编撰、所载阳明临终遗言为“此心光明,亦复何言”的《年谱》,刊刻于隆庆六年(1572)的全书本。同样是绪山负责编撰的,还有早于全书本,即成书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刊刻于嘉靖四十三年(1564)的嘉靖本《年谱》15。嘉靖本《年谱》也载有阳明生命最后时刻,特别是临终遗言的内容,其中“十一月丁卯,先生卒于南安”条下载:
是月廿五日,逾梅嶺至南安。登舟时,南安推官门人周积来见……遂问道体无恙否。先生曰:“病势危亟,未死者,元气耳。”侍者垂泣,以家事、嗣子问。先生叹曰:“何须及此。”少顷曰:“惟未得与诸友了学问一事,为可恨耳。”时时作越声,讶吉安何无一人至者。廿八日晚泊,问:“何地?”旁对曰:“青龙铺。”明日,召积入。久之,开目视曰:“吾去矣!”积泣下,问“遗言?”微笑曰:“此心光明,复何言?”顷之,瞑目而逝,盖二十九日丁卯辰时也。16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全书本《年谱》是嘉靖本《年谱》编入《全书》而形成的特殊版本,如果依据《年谱》来讨论阳明生平及临终遗言,那么相对于全书本,嘉靖本无疑更具有优先性。具体就嘉靖本《年谱》此处文本来看,结合上文不难发现如下信息:其一,同于后来全书本,嘉靖本《年谱》也载有周积向阳明问遗言,阳明答之曰“此心光明,复何言”的内容;其二,与全书本相比,嘉靖本载有侍者以家事、嗣子问,阳明在作“何须及此”之叹后,答之曰“惟未得与诸友了学问一事,为可恨耳”的内容,后者则无。就第一方面而言,上文已指出,《年谱》中记载周积向阳明问遗言的情形,与绪山在《哀感》《当道书》的相关说法相矛盾。考虑到《哀感》《当道书》在所作时间17皆早于嘉靖本《年谱》的情况,完全可以依据二者的记述判定嘉靖本《年谱》中所载为非,即所谓周积向阳明“问遗言”的情形,当是后来绪山编写《年谱》的人为设计,并不符合阳明最后时刻的实际。就第二个方面而言,嘉靖本《年谱》所载的内容,显然与黄绾《行状》中家童问,阳明答曰“他无所念,平生学问方才见得数分,未能与吾党共成之,为可恨耳”的记载相一致。这不仅反证黄绾《行状》所载内容的客观性和权威性,更表明绪山在编撰《年谱》中阳明临终情形时,对黄绾《行状》中的相关记述有着直接的借鉴吸取。
综上信息,不难发现以时间先后而论,阳明临终遗言存在黄绾《行状》、嘉靖本《年谱》,以及嘉靖本《年谱》编入《全书》而形成的全书本《年谱》三种文献。对比三种文献所涉阳明临终遗言的内容,存在如下两个信息:其一,相对于黄绾《行状》所载“他无所念,平生学问方才见得数分,未能与吾党共成之,为可恨耳”,嘉靖本《年谱》在对前者直接吸取,表述为“惟未得与诸友了学问一事,为可恨耳”的情况下,增加了“此心光明,复何言”的内容;其二,相对于嘉靖本《年谱》,全书本《年谱》则删除了前者的“惟未得与诸友了学问一事,为可恨耳”,只保留“此心光明,亦复何言”的记载。在此,存在两个问题:
就第一方面而言,绪山在编撰嘉靖本《年谱》中,为何在对黄绾《行状》所载文本有直接吸取的同时,人为增加周积问阳明遗言,阳明答“此心光明,复何言”的内容? 对此,并没有直接的文献说明其中理据,但基本可以确定,这与整个中晚明对阳明的推崇与“神话”有直接关联18。径直言之,作为弟子的绪山,为了彰显与推崇阳明“正面”形象,在编撰《年谱》过程中杜撰了周积问阳明遗言的情形,增加了阳明答“此心光明,复何言”的记载。当然,这也就意味着无论绪山在嘉靖本《年谱》中人为增加该部分记载的理据与目的何在,阳明临终遗言非“此为光明,复何言”,而更应该如黄绾《行状》所载。
就第二方面而言,在原载有“惟未得与诸友了学问一事,为可恨耳”的情况下,绪山为何在将嘉靖本《年谱》编入《全书》过程中删除该内容,只保留“此心光明,亦复何言”的记载?对此,显然可以从嘉靖本到全书本《年谱》的编撰原因作答。单就绪山而言,并未看到其对从嘉靖本到全书本《年谱》的编撰原因和过程的具体说明,这不免增加回答该问题的难度。不过,鉴于全书本《年谱》是嘉靖本《年谱》编入《全书》过程中形成的特殊版本,可以从《全书》刊刻的角度来回答这一问题。关于《全书》的刊行过程,此处限于主题不作具体考察,但可以明确的是,《全书》的刊行与阳明从祀孔庙有直接关系。对此,朱鸿林明确指出,由于参与刊行《全书》之人实际参与了朝廷关于阳明从祀孔庙的争议与过程,因此可以判定《全书》的刊行与阳明从祀孔庙有直接的关系19。换言之,《全书》的刊行是为阳明从祀孔庙的“大局”服务。具体到《年谱》,则当如杨正显所言,从嘉靖本到全书本的增减和删改,正是为了阳明从祀孔庙,即塑造一个合于从祀孔庙标准的阳明20,阳明从祀孔庙是嘉靖本到全书本《年谱》增减和删改的标准和目的。综合朱鸿林、杨正显的研究及观点,意味着嘉靖本《年谱》所载的“惟未得与诸友了学问一事,为可恨耳”(也包括黄绾《行状》原有的文本),并不符合阳明从祀孔庙的标准,需要予以删除。毕竟相较于“此心光明”的“正面”,“为可恨耳”这样的“负面”内容显得与从祀孔庙“不合时宜”。
总之,阳明临终遗言,从黄绾《行状》“他无所念,平生学问方才见得数分,未能与吾党共成之,为可恨耳”,到嘉靖本《年谱》“惟未得与诸友了学问一事,为可恨耳”,“此心光明,复何言”,再到全书本《年谱》“此心光明,亦复何言”,存在从黄绾《行状》到嘉靖本《年谱》的增补,再从嘉靖本《年谱》到全书本《年谱》的删减过程。进而,基于三者有关阳明遗言的具体内容,以及彼此之间从增补到删减的关系,足以表明黄绾《行状》所载的“他无所念,平生学问方才见得数分,未能与吾党共成之,为可恨耳”才是阳明临终遗言的实际,阳明临终情形的见证人为家童、侍者,而嘉靖本和全书本《年谱》所载门人周积问“何遗言”,阳明答“此心光明,亦复何言”的内容,则出自绪山等《年谱》编写者的杜撰,反映的是对阳明的推崇以及阳明从祀孔庙的大局。
三
上文表明,嘉靖本《年谱》是考察并确定阳明临终遗言的关键,嘉靖本与全书本《年谱》之间存在内容上的差异。鉴于学界对嘉靖本《年谱》,以及嘉靖本与全书本《年谱》之间的同异少有介绍讨论,本节拟对两种《年谱》所载内容中重要而显著者略作文献上的比较考察,在呈现二者内容上具体差异的同时,对其中原由及意义作一定分析。
阳明思想形成发展中,发生在弘治五年壬子(1492),阳明21岁时的“格竹”是重要事件。其中,嘉靖本《年谱》在“五年壬子,先生二十一岁,在越”条下载:
始在京师,遍求考亭遗书读之。因思先儒谓“众物必有表里精粗,即一草一木,皆涵至理,不可不察。”官署前多竹,即取竹格之;苦求其理不得,病作而止。乃贬志,为辞章之习。21
全书本《年谱》同条的记载则为:
是年为宋儒格物之学。先生始侍龙山公于京师,遍求考亭遗书读之。一日思先儒谓“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官署中多竹,即取竹格之;沉思其理不得,遂遇疾。先生自委圣贤有分,乃随世就辞章之学。22
比较来看,全书本相较于嘉靖本有两点主要差异:其一是将此条的内容揭标为“是年为宋儒格物之学”,其二是增加了“先生自委圣贤有分”的文字。就第一点来说,首先体现的是对格竹事件及性质的概括,将格竹与阳明18岁时在迎亲途中“始慕圣学”而拜访娄谅(1422-1491),娄谅“语宋儒格物之学”,谓“圣人必可学而至”23联系起来,突出阳明思想形成发展过程中,尤其是格竹一事与宋儒(朱子)格物之学的关联。就第二方面言之,体现了绪山自觉把格竹事件与阳明在成化十有九年癸卯(1483),12岁之时“读书学圣贤”关联起来,这不仅意味着早年读书学圣贤是格竹的内在动力,也表明“圣贤有分”的困惑与紧张是推动阳明思想进一步变化与发展的问题意识。当然,这样的分析和结论构成了相对于嘉靖本,绪山在全书本《年谱》中增补“是年为宋儒格物之学”和“先生自委圣贤有分”的理据与目的。
正德三年(1508)的龙场悟道是阳明心学思想的标志事件。对于龙场悟道,嘉靖本与全书本《年谱》所载也有不同。嘉靖本《年谱》“三年戊辰,先生三十七岁,在贵阳”条下载:
是年先生始悟格物致知。龙场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棘中……因念:“圣人当之,或有进于此者。”忽中夜思格物致知之旨,若有语之者,寤寐中不觉叫呼踯躅,从者皆惊。自是始有大悟,乃嘿记五经证之,因著《五经臆说》。24
全书本《年谱》该条下载云:
先生始悟格物致知。龙场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棘中……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乃默记五经之言证之,莫不吻合,因著《五经臆说》。25
枝节内容暂且不论,嘉靖本与全书本《年谱》在龙场悟道上最显著的差异在于,后者增加了为人熟知的“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即所谓“先生始悟格物致知”的龙场悟道的确切内容。如何看待全书本《年谱》增加该内容的意义?可从两方面略作回答:其一,单就嘉靖本《年谱》所载龙场悟道来看,事实上并不能对其中所谓“是年先生始悟格物致知”的具体所指有一确切结论,这或许是绪山在全书本《年谱》中增补“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的原因;其二,与前一方面内容相关联,如果绪山在编撰全书本《年谱》时未作内容上的增补,而是径直采用嘉靖本《年谱》的记载,意味着我们在考察龙场悟道时,必然会出现不同的问题与面向。换言之,如果基于嘉靖本《年谱》的记载,即无“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的内容,那么当如何把握“是年先生始悟格物致知”的具体所指?如何理解和定位“龙场悟道”的内涵与意义?
在将嘉靖本《年谱》编入《全书》,形成全书本《年谱》过程中,绪山还增加了一些按语。全书本《年谱》正德“五年庚午,先生三十九岁,在吉”,“十有二月,升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论实践之功”条(嘉靖本《年谱》无此揭标)下,绪山有云:
按:先生立教皆经实践,故所言恳笃若此。自揭良知宗旨后,吾党又觉领悟太易,认虚见为真得,无复向里着己之功矣。故吾党颖悟承速者,往往多无所成,甚可忧也。26
此条按语不载于嘉靖本《年谱》。绪山为何要在全书本《年谱》中增补这一内容?结论言之,绪山增加此按语,是针对阳明提出良知宗旨后,“吾党又觉领悟太易,认虚见为真得,无复向里着己之功”,“吾党颖悟承速者,往往多无所成”“可忧”现象的有感而发,融入了绪山对后学有悖于阳明“实践之功”思想现象的批判性思考。换言之,阳明后学中一些思想现象与问题成为绪山反省批判的对象,并影响其在将嘉靖本《年谱》编入《全书》,形成全书本《年谱》过程中的编撰。
加上前文临终遗言及这里格竹、龙场悟道、实践之功条下之按语,表明嘉靖本与全书本《年谱》在内容上存在差异。从嘉靖本到全书本《年谱》有具体内容上的删减与增补,也有揭标的概括和按语的增加。而从嘉靖本到全书本《年谱》的增减与修改,除了前文提到的阳明从祀孔庙外,还有绪山对阳明思想的理解和概括,以及对阳明后学中一些思想现象的反省等原因。
综上所论,从黄绾《行状》到嘉靖本《年谱》,再到《年谱》全书本,体现出以“为可恨耳”“此心光明”为内容的增补到删减的过程与关系,表明黄绾《行状》所载的“他无所念,平生学问方才见得数分,未能与吾党共成之,为可恨耳”方为阳明临终遗言的确切实际,阳明临终遗言的见证者是侍者、家童,而非门人周积。相对于黄绾《行状》中的“为可恨耳”,嘉靖本与全书本《年谱》增补和保留的“此心光明”,反映了后学对阳明的推崇,以及服务于推动阳明从祀孔庙的大局。总之,阳明临终遗言是“为可恨耳”,而非“此心光明”。此外,以“临终遗言”“格竹”“龙场悟道”“论实践之功”条下之按语为内容作考察,显示绪山将嘉靖本《年谱》编入《全书》、形成全书本《年谱》过程中,存在内容上的增减和删改。阳明从祀孔庙、对阳明思想的理解概括以及对后学中某些思想现象的批判反省,构成绪山在编撰全书本《年谱》过程中作增减删改的原因。嘉靖本与全书本《年谱》在具体内容上的差异及其意义,值得作更全面的讨论。
注释:
1本文的《王文成公全书》的文献依据是[明]王守仁撰,吴光、钱明等编校:《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下文相关引文均引自此版本,不再赘述。
2《阳明先生年谱》有全书本和嘉靖本,关于两个版本之间的关系和差异,详见下文论述。
3[明]王守仁撰,吴光、钱明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第1463页。
4按照地域划分,周积属于浙中王门,然黄宗羲《明儒学案》未载其学行。
5[明]王守仁撰,吴光、钱明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第1579页。
6陈来已注意到全书本《年谱》与黄绾《行状》记载上的差异,但未作明确结论。(参加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398—399页。)
7[明]王守仁撰,吴光、钱明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第1537—1538页。
8同上,第1543页。
9钱明:《王阳明及其学派论考》,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4—108页。
10张宏敏:《黄绾道学思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128页。
11[明]王守仁撰,吴光、钱明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第1601页。
12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第399页。
13[明]王守仁撰,吴光、钱明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第1603页。
14邹建峰:《阳明夫子亲传弟子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78页注释。
15关于全书本与嘉靖本《年谱》之间的关系,径直言之,全书本是嘉靖本在编入《全书》过程中形成的特殊本子,即《全书》卷32-34的内容。
16[明]钱德洪编、罗洪先考订、龚晓康等点校:《阳明先生年谱》,龚晓康、赵永刚主编:《王阳明年谱辑存》,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62页。此点校本以刊刻于嘉靖四十三年(1564)的《阳明先生年谱》为底本。
17绪山《当道书》所作时间不可考,但应早于《年谱》完成的时间。
18钱明:《从“圣域”走向“神坛”的王阳明——中晚明神话王阳明的当代警示》,《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19朱鸿林:《〈王文成公全书〉刊行与王阳明从祀争议的意义》,《孔庙从祀与乡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125—150页。
20杨正显:《王阳明〈年谱〉与从祀孔庙之研究》,《觉世之道:王阳明良知说的形成》,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85—323页(附录二)。
21龚晓康、赵永刚主编:《王阳明年谱辑存》,第12页。
22[明]王守仁撰,吴光、钱明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第1348—1349页。
23同上,第1348页。
24龚晓康、赵永刚主编:《王阳明年谱辑存》,第20页。
25[明]王守仁撰,吴光、钱明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第1354—1355页。
26同上,第1358页。
图文收集与编发:中国文化书院(阳明文化研究院)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 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