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第2期《教育文化论坛》刊载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教授王胜军博士、贵州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副教授蔡丹博士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宋明理学史新编》”(17ZDA013)研究成果,题:沙滩文化与程朱理学。全文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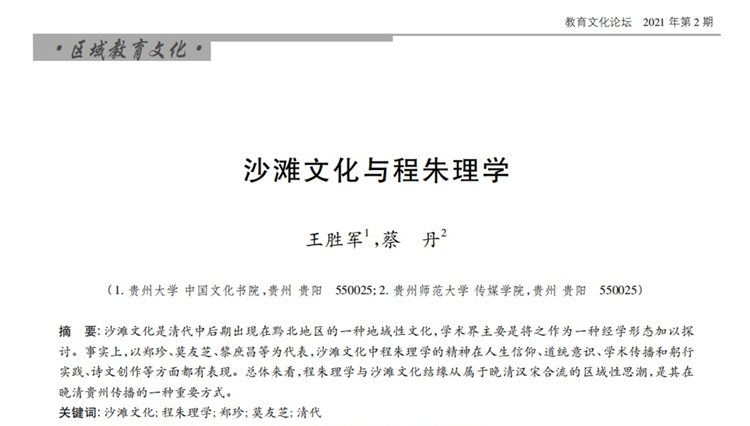
摘要:沙滩文化是清代中后期出现在黔北地区的一种地域性文化,学术界主要是将之作为一种经学形态加以探讨。事实上,以郑珍、莫友芝、黎庶昌等为代表,沙滩文化中程朱理学的精神在人生信仰、道统意识、学术传播和躬行实践、诗文创作等方面都有表现。总体来看,程朱理学与沙滩文化结缘从属于晚清汉宋合流的区域性思潮,是其在晚清贵州传播的一种重要方式。
关键词:沙滩文化;程朱理学;郑珍;莫友芝;清代
基金项目: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宋明理学史新编》”(17ZDA013)
清代贵州遵义沙滩文化,广泛地表现在学者群体的价值取向、学术旨趣、生活方式、艺术追求、政治理解等方面,尤以汉学最为亮色,故一般都更多注意其汉学特质。事实上,沙滩文化中的不少学者都是程朱理学的信徒,其学术表现出“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的特征。程朱理学依托汉学传播,是清代理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目前,学术界对沙滩文化与程朱理学的关系已有所认知和论列1,但仍有必要进行专门探讨和深入梳理。本文以郑珍、莫友芝、黎庶昌等学者为中心,探看沙滩文化与程朱理学的关系,兼以考察清代黔学的内部结构以及士人的文化心理,敬请方家不吝指正。
一、基本的价值取向
价值取向包括世界观、人生观、历史观、正统观等诸多方面,是超越具体知识、制度和文化的一种形而上的理念,是士人立业修身的一种心理支撑和终极追求。程朱理学是沙滩文化学者精神领域中各种理念的总和、趋向以及面对大千世界的抉择准衡。
1.尊信程朱之道
沙滩文化以黎、郑、莫三家为代表。黎氏家族中,黎怀仁、黎安理、黎恂等一直崇信程朱。黎怀仁临终时所讲“平生半学朱元晦”[1]1 059,就是对黎氏家风、家学的一个定调。黎安理“制举之文,上逼国初诸老”[2]107,著有《四书蒙讲》,浸淫程朱之学自不待言。汉学既兴之后,沙滩文化学者即将之与程朱理学结合,如黎恂之晚年,“经则以宋五子为准,参以汉魏诸儒,史则一折衷于纲目”[3]111。宋五子即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而纲目则指朱熹所纂的《资治通鉴纲目》。可见,从文化观、历史观上黎恂都属程朱一脉。
在稍晚一辈的沙滩文化学者中,郑珍对程朱理学的尊信最为突出,如黄万机称程朱理学是其“哲学基础或基本的治学原则”[4],施吉瑞则称朱子学为其“早期的思想资源”[5]121-122。考察其生平,郑珍少时认识到“既浅俗学为不足尚,尤惩涉猎为无所归,自忖非潜心宋五子之学,无以求圣人至道,终不能济古儒者”[6]704,于是在舅父黎恂的指导之下,学业得以大进。黎恂去世之后,郑珍亦以程朱道统称述之,《祭舅氏黎雪楼先生文》开篇即道:
呜呼!释氏论人,四大合成。当其散时,无影无因。虽则云然,是气非理。气则有终,理则无止。孔、曾、颜、孟,周、程、邵、张,惟其理存,至今不亡。维我舅氏,我知不朽。……生存没宁,乘化以游……所谓理者,止如此焉……[7]586-587
可以看出,在郑珍的世界观中,认为佛教只看到了气之有终有散,而未看到儒家之理的亘古长存,孔、孟、程、朱等先贤就是以理而长存于天地之间。佛教对死亡忧心焦虑,不及张载《西铭》“存,吾顺事;没,吾宁也”更加坦率与自然。其子郑同知追述郑珍之言说:“朱子一生精力尽在《四书集注》,根柢尽在《近思录》,吾五十以后,看二书道理,历历在目前滚过,稍涉影响,便有走作。”[6]708-709可见,程朱理学是郑珍晚年精神信仰的走向。
对莫友芝而言,程朱理学同样是其“人生志趣”[8]290-294。据其日记记载,同治五年(1866)农历七月初八,莫友芝在龙门讲舍,曾以隶书二纸,誊写张载《克斋铭》及朱熹《敬义斋铭》(一说乃宋儒真德秀作)[9]189。两铭均收录于清人张伯行《学规类编》之中。铭是刻于器物上的自警之词,如《大学》“汤之盘铭曰: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张载《西铭》《东铭》亦是此类。《克斋铭》是张载理学世界观、工夫论的体现,如“惟人之生,父乾母坤。允受其中,天命则存……动静以察,晨昏以思。良知固有,匪缘事物。卓然独见,我心曒日。物格知至,万理可穷。请事克治,日新其功……”[10]229,讲到人与天地的关系及察识的修养方法。朱熹《敬义斋铭》同样是讲以天道来约束自身:“惟坤六二,以德直方。君子体之,为道有常……大哉敬乎,一心之方;至哉义乎,万事之纲。敬义夹持,不二不忒……”[10]229历来以《敬义斋铭》自警者多有之,比如明末清初学者侯岐曾就曾将《敬义斋铭》刻置于座右。
越是在忧苦繁难之际,程朱理学越往往成为一种精神支柱。郑珍一生贫病不得志,在《与莫茝升书》中自述说:“今年坐荒山中,穷到无去处……然其中似少有所得,朱子谓须有背地八九年,非欺我也。今虽精疲血衰,十五不及当年,自计尚可支持十许岁,得粗有闻见。而非天地生我,父母育我,庶几瞑目。”[7]452-453莫友芝亦曾以程朱自比,在《遵义府志》编成之后,却饱受争议,而且还有人煽动无赖对郑、莫两人动武。在莫友芝看来,程、朱讲明孔孟之学,为后世仰为“泰山北斗”,然而程颐被诽谤为“无乡行”,市井之人目为“五鬼之魁”;朱熹之学也被禁为“伪学”,横被不忠不孝等十罪;世人对自己和郑珍的诽谤,亦如程、朱当时之情形[11]509。
2.批判心、释之学
由于王阳明的亲炙和黔中王门的活动,贵州长期以来都是王学传播的重要地区,但在科举制度的影响之下,程朱理学在士子中间广泛传播仍然是一个事实,只是没有占据学术舆论的中心,到清代中期陈法这样尊朱辟王的学者产生之后,学术史的风貌才发生了转折。
到清代晚期,肯定王阳明又批判王学成为沙滩文化道统意识的重要表现和特色。郑珍、莫友芝等人对王阳明本人的事功和学术报以热烈的倾慕与歌颂,如郑、莫及黄彭年曾于咸丰五年(1855)游览贵阳阳明祠并留有诗作,还曾参与过黔西州道光二十七年(1847)即王阳明诞辰之375周年祭祀典礼,亦留有诗文。然而,在道统和学术上,郑、莫对王学却多有排斥,如郑珍以“程子敬邵子者也,而不甚重其说《易》;朱子敬张子者也,而不尽醇其《正蒙》”[7]512为榜样,对王阳明亦是敬其人而黜其学,并认为前人陈建、张烈、陆陇其等已对王阳明的学术进行过清算。郑珍对王学从学术角度加以批判说:
佛实而儒名者,何以异是?……若象山、阳明诸子,其可惜乎!既慕佛、老之术为甚深妙,不仙佛则恐虚此一世也;而又虑不孔、孟则得罪于世教,竭大过人之才力,使佛、老昏塞其脏腑,而号于人乃曰:“吾孔孟之道也。”……吾观朱子自道其资质要不过中人,视象山四岁时即思及天地穷际者,固远不及矣,乃卒得圣人之纯正。[7]520
《学蔀通辨》是明代学者陈建的辟王论著,郑珍观此而生发议论,认为王学是援佛入儒。从道统上,莫友芝对王学褒中有贬,如其诗:“末流狂肆到西来,歧路还凭快马催。妄说晚年传《定论》,何伤盖代作雄才。圣贤不是冥搜得,勋业端能至道该?为语高明诸后秀,漫言空旨误滋培。”[12]354在莫氏看来,王学发展到后来就是末流狂肆,《朱子晚年定论》更为后人伪托。
辟佛更为明确,韩愈《原道》为了树立儒学正统,就首开对佛道两教的激烈批判,这成为后来儒家士人道统意识的一种表现。黎庶昌的父亲黎恺就曾表示说:“延寿算,求功名,望子息,禳祸灾,此是世俗通情,然必持斋念佛,作僧道家言,吾不愿也。”[13]2郑珍在《甘秩斋黜邪集序》中也指出,“佛之行背伦弃常,广张罪福以资诱胁”“其言弥近理,弥大乱理,力足使命世豪杰甘心纳身为夷狄”,士人习佛而自以为儒,致乱学术、乱天下,程朱“辟其言”即从理论上辟佛较之韩愈更有意义,因为这能使民众“醒天良,生感悟”[7]462。同样,莫友芝也曾在《盂兰会》一诗中对佛教加以批评,描绘出遵义西乡“肥僧臭道斗啗唱”的景象[12]495。莫氏认为,佛教不仅不能救世,并于诗中自注该地佛教虽昌盛却数年内发生有杨凤、邹辰保之乱。莫友芝由此诘问道:“此时佛法何处救?袖手低眉泥土蹲。故知平等匪真惠,长恶翻结无穷冤。”[12]495莫友芝在这里主要是批评佛教不别善恶的平等思想,这不仅使人联想到王学的心体“无善无恶”之说,也是辟佛、辟王往往结合在一起的原因,而程朱理学在这方面与佛教的界限更为清楚。
二、主要的学术内容
具体来看,沙滩文化学者几乎没有与程朱理学相关的论著,却非常注意从版本目录学角度对程朱理学的相关文献进行整理,这也形成了与程朱理学结合的一个方式。此外,在其汉学研究过程中,亦往往不吝兼采程朱的观点。
1.整理程朱学文献
程朱学文献是士人业举的参考书,郑、莫、黎等家族专心于程朱理学,自然广览熟知,不过当时书院、学宫所藏多是《御纂四书讲义》以及《四书五经大全》等普及本且范围狭窄,程朱学诸书仍然有其搜集意义。同治二年(1863)八月,莫友芝函问其弟庭芝,感慨王白田《朱子年谱》未之能见[11]649。同治六年(1867)六月以讫年末,莫友芝在上海购买了《伊洛渊源录》《朱门授受录》《汤子遗书》《陆子余集》等[9]232-233。之后,又购有《二程遗书》和元本《伊洛渊源》[9]261-262。
对于版本的追求,最终形成了莫友芝的一部辑轶之作,即《十先生中庸集解》(简称《中庸集解》),成书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八月。该书内容原为宋代新昌人石 乾道间所集周敦颐、二程、张载及其门人吕大临、谢良佐、杨时、游酢、侯仲良、尹焞等十家之说。朱熹为之作序,谓其谨密详慎。十年之后,删为《辑略》,仍以原序冠之,后又为《或问》以明诸家之纯驳。淳熙间,《中庸章句》成,以《辑略》《或问》附后。《辑略》既行,《集解》遂微,如尹焞之说遗失,而增之以司马光、王安石。元代时已罕见其书。莫友芝于是依托卫湜《礼记集说》中十家之说,钞出并复原该书。
乾道间所集周敦颐、二程、张载及其门人吕大临、谢良佐、杨时、游酢、侯仲良、尹焞等十家之说。朱熹为之作序,谓其谨密详慎。十年之后,删为《辑略》,仍以原序冠之,后又为《或问》以明诸家之纯驳。淳熙间,《中庸章句》成,以《辑略》《或问》附后。《辑略》既行,《集解》遂微,如尹焞之说遗失,而增之以司马光、王安石。元代时已罕见其书。莫友芝于是依托卫湜《礼记集说》中十家之说,钞出并复原该书。
晚清杨园学对当时思想界有着特殊的影响,贵州亦不例外。据郑珍自述,其成童之时,舅氏黎恂自桐乡返,即从之受业,见《杨园先生全集》后读而爱之。之后,郑珍时举张履祥《见闻》《近古》二录中言行语,同辈“以不见是书为恨”[7]459,而郑珍自己亦恨仅有手抄节本。莫与俦在京城庶常馆时就借读过《杨园先生全集》,来遵义讲学时,又向莫友芝等推荐此书,并叙述清初学术渊源,在莫与俦看来:“国朝两儒宗,曰潜庵、稼书。潜庵之学,承之新吾、苏门;稼书之学,开之蕺山、杨园……三鱼堂学术诸辩说,杨园盖已三致意焉……孔孟道乃复明。”[14]19之后在同治四年(1865),莫友芝曾受高伯坪所赠《张杨园年谱》[9]167。正是因为郑、莫两家有其共同的学术志趣,所以在编纂《遵义府志》的过程中,郑珍有幸找到该书时,就与莫友芝合刻,时为道光二十一年(1841)。当时莫友芝白之其父,莫与俦极高兴地说:“吾向欲雕《人谱》、《呻吟语》等书,以其本易得,辄止。所拳拳杨园数十年矣!好雠之,亦以毕吾志。”[14]20在该书序言中,郑珍历数杨园全集的版本渊源,称其“学之醇,行之笃,可为法于天下,传于后世”[7]459,又举张履祥《与何商隐书》中“《近思录》之刻,恶必人之宝爱,但以昔日所见此书之幸,与今日求觅此书之难,度亦此心为人心之同然耳”表示自己刊刻杨园全集,就是私淑张履祥刻《近思录》之志,是为传播程朱理学,而非阿世媚俗[7]459-460。这说明,杨园之书在当时既不易得,其学亦不是一种显学,时距杨园从祀孔庙之同治十年(1871)尚有三十年之久。此外,郑、莫合刻的是朱刻全集本即蜀山堂本,在版本学上具有一定意义。
此外,莫友芝还收藏有朱熹书卷真迹,如朱熹《戒自弃文》,宋编《晦庵集》《续晦庵集》《晦庵别集》均未收录,直到清雍正朝朱玉刻《朱子大全文集类编》,始与《童蒙须知》《从学帖》等摭附全书之末。莫友芝又阐述其意义说:
虽类编之刻,掺割无绪,七阁《四库》黜诸存目,而此文之提掖警切,固与《童蒙须知》等,与远行登高、植基启涂,开于来学甚钜,则旧编所不应逸者也。[14]177
同治九年(1870),曾国藩将《戒自弃文》选善手拘镌,致之湘乡家祠私塾中,以诏族之子弟。郑珍也辑佚有朱熹真迹七言绝句四首一卷,并加以考证说明。[7]560又有世传朱熹校定《上蔡语录》三卷,郑珍认为前人增补不当,应该一还朱熹之旧,并计划令其子依其说别写一本,为朝夕服膺之用[7]556。此外,黎庶昌也核覆过元至正六卷本《程氏易传》[15]248。
2.融汇汉宋两家
朱熹是宋学的一派宗师,其实也擅长考据,并被章学诚认为是清代考据学的远祖,近人姚永概亦提及朱熹《韩诗考异》为清代校勘学之先河[16]1-2。在郑珍看来,汉、宋之学并无本质差异,“程朱未尝不精许郑之学,许郑亦未始不明程朱之理。”[3]157就经义考证而言,郑珍在与莫庭芝的信中亦曾指出:
近通治《周礼》,几尽部。朱子谓经疏,《周官》最好,细看,果然。朱子说经,匝实明白,正是深此家法,故秤等不差耳。[7]453
在探讨到具体礼仪如“女子子嫁者、未嫁者为曾祖父母”时,因为朱熹对郑玄之说先存疑而后认同,郑珍就发挥说:“朱子特以郑氏讲礼之宗,终不肯违其说”[17]48。关于婚礼“南洗”“北洗”的问题,郑珍认为朱熹作《家礼》依郑玄“南洗”“北洗”均在室中而非室外之意,发议论说:“愈见朱子于郑义无微不等秤过,胜司马诸人远矣。”[17]66相反,于清代汉学家如戴震、阮元等,郑珍却不无驳斥,谓其“粗心”[17]52。郑珍在解说《孟子》时,多认同朱熹之说,如“粪其田而不足”句,赵岐之注为“凶年饥岁,农人粪治其田,尚无所得,不足以食”,作“不足以自食”解。全句为“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年,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郑珍认为是农人辛苦劳作,仍不足贡其赋役,可与前句“寡取之”呼应,并以朱熹“益之,以足取盈之数也”来为自己辩护。至于近世讲家为“不足偿粪田之费”,郑珍就批评说于“通节词理俱不从顺矣”[17]37。对“下达,纳采,用雁”的解释朱熹讥郑玄不通,郑珍在《仪礼私笺》中亦加以肯定[18]18。
当然,郑珍对朱子之学亦有商榷。如考证韩愈《与大颠三书》时,郑珍就认为该书是“词鄙衔谬,已可断为庸妄人所假托”,尽管朱熹“坚与弥缝”,而第一书却“万万不能弥缝也”[7]553。又如《孟子·告子下》中的“王豹”,赵岐注之为“卫之善讴者”,朱熹因之曰“豹,卫人也”,而郑珍自己据《左传》杜注考察,认为王豹应该是齐人[17]38。
莫友芝以版本目录学著称,很少涉及具体学术思想。不过,在《中庸集解》一书中,莫友芝仍然通过校勘对比表现自己的态度,如《辑略》于《中庸》首三章解后继以章句题解,是一篇之体要,关乎道之本原、存养省察等要目,而《中庸集解》却付之阙如,莫友芝就随条附校,增入其中[19]62-63。在黎庶昌眼中,朱熹与子夏、郑玄被作为“章句三大儒”,有“研经宗汉”之旨,不应被世儒所讥评[15]55。又称程氏《易传》“深造自得”“与圣人者性命之旨合”[15]144。不过,黎庶昌更多倾向于以汉学解程朱。
三、践履及诗文创作
与整个清代理学的发展特征一样,沙滩文化中的程朱理学同样远离心性理气等概念解析,从而走向生活、社会的伦理践行。同时,沙滩文化学者还积极进行文学创作,借以鼓吹程朱之学的价值理念,又表现出理学与诗文相兼发展的特征。
1.躬行践履
躬行践履是清代理学的一个重要特色,相比较而言,宋明时代更加注重于概念发明和理论创造。明亡之后,实学思潮兴盛一时,批判理学空疏成为主流,程朱理学代王学而兴起,同时也改变了自身玄谈的风格,转之而变为笃实践履,从北方的孙奇逢到南方的张履祥都是这种新理学的代表。
沙滩文化学者在言行等方面都努力去践行程朱理学,就有学者认为黎氏家族始终坚守程朱理学的“敬恕”论,强调个体人格的至善[20]。如黎安理是“终日坐必端,行必正”,而且“夜深,笔覆帽,书还秩,缺衣叠庪,晨兴而更始之,终身不衰”[3]81-82。其继母夏氏为人悍虐,活到九十多岁,晚年得怪病,黎安理在旁边侍奉汤药数十日,毫无倦容[21]49。其子黎恂同样是如此,自谓“士学程朱必似此真体实践,始免金溪、姚江高明之弊”[3]111。史载其“生平不苟言笑,立不跋倚,坐必端,行斋如流,老无滕待,暑无袒衵,非靧不科头,非疾不晏起。居处虽微物度置必当,书卷经百十过常新整若未触手”[3]113。可谓深得朱熹整齐严肃、敬义夹持的精神,而与阳明学疏狂进取的形象大异其趣。即便是在七十生日之际,黎恂仍然是“守程朱遗训,不乐不,追惟纲极”[7]468-469,保持着恭敬肃穆的态度。
程朱理学包括杨园学对郑珍的人生践履亦有重大影响,其性格气质乃是长期浸淫于性理之学的结果[22]。郑珍一生清贫,又久屈场屋。然而,正是在这种清贫中,体悟着程朱理学的处世精神,在其看来:“大抵吾辈读书,求知难,能行更难。然必能行得一分,始算得真知一分。”并且引用朱熹的话说:“其知也,其行也,表理精粗,无不到也。”[7]452莫友芝、郑珍在京城应试时,就表现出《近思录》中要求的“出处进退辞受之义”,正如黄万机所描述的:“由于他俩在寓所中‘闭门赏析’古籍,不干与世事,反而惹起他人的‘物议’。一般举人入京应试,总要去奔走要津,干谒权贵,以求靠山。”[8]38
程朱理学在沙滩文化的教子、治家中都有表现,如郑珍面对晚清混乱的时局之变说:“世变,道终不变耳。”又曾担心说:“卯儿总不嗜程朱,终日忙忙,东繙西阅,于圣人之迹且不能粗见……”[7]453郑珍送黎庶昌到武昌投亲并赴顺天参加乡试时亦以“孔孟之所为教,程、朱之所为学”[7]476对之加以激励。莫友芝在其《甲辰家规》第三条“亲劳辱”中也指出:“《曲礼》、《少仪》、《内则》、《弟子职》诸书,最为详悉,故朱子以扫洒应对进退为小学,作圣之基,实在于此。”[14]375黎庶昌在《黎氏家祠记》讨论祭祀渊流,亦指出:
惟独伊川程子,以谓高祖有服,无贵贱皆当祭及高祖,朱子从之,后世垂为定制。盖其言深原礼意,协乎人心,天属之至安而无以易也。[15]209
早先,黎庶昌二世祖黎怀仁就表示死后“丧葬以礼,不要浮屠”。郑珍在其父母去世时效法邵雍,以其力办所及者;其及嘱后身后之事,亦要求用程颐之法,不要烧纸钱,即不学浮屠之法[7]610。
最后,表现在以程朱理学观念改造当时的教育和政治生态。比如,作为山长的郑珍曾将朱熹《弟子职》章句笔之于启秀书院之垩壁,原因在于《弟子职》“难得传本,因罕读者”,更重要的就是要求生徒以之躬行实践。黎庶昌《上穆宗毅皇帝第二书》认为,朝廷应参照朱子之议,对科举考试体系进行改革,并将周、程、张、朱、陆等学术作为科目之一[15]42。
2.诗文创作
晚清诗文创作深受程朱理学影响。散文以桐城派蔚为大宗,主张作文要贯穿程朱之学的“义法”,目的就是“因文见道”[15]65,非徒为文辞之美。前期如方苞、中期如姚鼐都是代表人物。到晚清,曾国藩及弟子如黎庶昌、薛福成、吴汝纶等将之继续发扬。诗歌主要表现为宋诗派的崛起。
沙滩文化既有经学的性格,又有诗文的风致。文学成就最高者首推郑珍、莫友芝、黎庶昌三人。从思想内容上看,以道艺合一的精神宣传节义之士,将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观点渗透在历史人物的叙事之中,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如《遵义府志》即编有《列女传》两卷,表扬其贤明、贞烈、守节、才艺等。其中,最重要就是宣扬程颐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不少本身无事可纪,亦标以“夫死,守节”“夫死,力贫扶孤”“夫死,上奉夫家三世,下抚遗孤”。其中,庠生周鸿仕妻黎氏,夫病割股救之,夫既死,又抚育孤子,其嫂图谋其家产,逼之改嫁,屡遭迫害,以致数死。后来回到娘家,有人劝其改嫁,黎氏云:“无此孤,吾犹不为狗彘行,况尚有周氏一脉乎?”[23]207于是带着孩子拾薪苟活。当然,郑珍也较为宽容地指出未婚守节并不可以为常道[17]28。贞节烈女之外,其他人物有忠节、孝友、行义等,不一而足,如李樾“苦心行己,介然离俗”[23]147,又如王道长“家贫力学,不忮不求”[23]159,又如吴湘“言行不苟”“凡过其侧身者必整肃衣冠,与言必慎唯诺”[23]161。当时,晚清贵州战乱不断,涌现出不少官方意义的忠孝节义之士,莫友芝《智烈冯童子墓表》就记述了一个被掳掠的冯姓童子,暗藏利刃于敌人食具之中,潜杀十七人的故事。莫友芝在传中称盛此童子说:“冯童子以宗慤拒劫之年,有区寄谲贼之智,用逢盛才美之述,为汪踦勿殇之铭,宜也。”[14]358这都表现了郑、莫基于程朱理学的观念和立场。黎庶昌是当时桐城派中兴的重要人物,作为曾国藩门徒,其文章尤其强调经世的意义[24]537。同时亦兼申述道统,如其名作《读王弼老子注》,就指出老子“元同以为体,因循以为用,无成势,无常形,不可与圣人吉凶、悔吝、忧患之旨合”,并以“甚矣,学深浅不可假也。朱子曰:‘王弼《周易》,巧而不明’,其知弼者欤”[15]144结其尾。
就诗歌而言,宋诗派反对晚明以来的“性灵说”,而主张“道艺合一”和“性情说”,批判严羽之类只讲体裁、趣味的诗论,反对“浮薄不根、流僻邪散”之作,同样是程朱理学精神在文学艺术领域中的发展。郑珍、莫友芝都是宋诗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如莫友芝就将深厚的学识、高尚的道德情操作为诗人之必要[8]346。郑珍同样认为“学其诗,当自学其人始”[7]465。甚至要儒行绝特、条理万物,才能于诗称圣、称大家[14]45。对诗歌的态度,程朱将之作为低层次的辞章之学,郑珍虽以诗见长,却不肯以诗人自居,莫友芝亦恐郑珍以诗人名世[14]46。从内容上,如郑珍《纪赵福娘姑妇三人死节事》《陈氏妇》都是对节烈孝义的歌颂。此外,表现在艺术形式上就是唐诗抒情,宋诗说理,即以议论为诗,如前述莫友芝“末流狂肆”一诗就非常典型[24],批判遵义西乡佛教盛行与地方社会动乱一诗风格亦是如此。
四、余论
关于汉学、宋学的关系,就历史发展而言,虽有汉宋之争这样一个事实,不过,其间的联系也非常值得注意,即钱穆所指出的“汉学诸家之高下浅深,亦往往视其得于宋学之高下浅深以为判”[26]1。有清一代,“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这一现象有着比较普遍的表现。很多时候,汉学作为一种知识形态成为承载程朱理学传播的载体。
首先,沙滩文化从知识体系上尊崇汉学,缺乏哲学思考,精神上需要程朱理学加以支撑。汉学自身虽然有以“小学明大道”的期图,学术界也试图勾勒出汉学反对宋学、建设自身道统的脉络[27],毕竟仍然主要是一种学术方法。汉学虽然可以对圣王时代的远古历史和制度作出详密考证,却无法构建起自身的意义世界和价值来源,汉代主要依托谶纬,清代不得不求之理学。程朱理学对汉学而言不是寄生的,而是具有灵魂的意义,并且是黔北地区科举与地方社会结合的一种表现。到同光年间,“随着整个儒学内部的变化、调节,调和汉宋的观点逐渐取得优势,成为一种学术发展趋势”[28]104,这也是对沙滩文化学术特质的说明。
其次,汉学与程朱理学结合的特点是知识体系与价值体系各司其职。程朱理学到清代收缩了关于概念的探讨和论断,成为汉学圣王制度世界缺乏人情义理和心灵安顿的一个补充。汉、宋两派追求的最终理想都是实现三代之治,从这一点上具有高度重合性。与陆王之学不同,程朱理学本就重视经验知识,讲求从圣贤语言中寻求义理的逻辑也与汉学比较一致,所以莫与俦就讲“《六经》堂构于汉儒,守成于宋程、朱诸子,而大败坏于明人”[7]497。在其看来,程朱、汉学都是在力揭六经之义,共同表现了自清初以来不断发展壮大的实学精神。这样,沙滩文化就与江藩等反宋学、反心性的倾向不尽相同。
最后,程朱理学的自我生发,承接了汉学的传入和发展。程朱理学在贵州不是显学,但拥有较长的发展历程。尤其是到乾隆中期,以贵山书院为中心,以山长陈法为代表人物,出现过一个程朱理学的高峰,这时的程朱理学传播主要是与科举制度结合,并依托八股文撰写来完成的。八股文虽然可以入仕,却严重缺乏现实关怀。晚清的特殊时代要求程朱理学有更多的转变,这样,沙滩文化学者就由程朱理学转而汉学、向着经世的方向前进。而汉学又大大丰富了原有沙滩文化中程朱理学的学术性格,增加了其内部的张力和活力。
参考文献:
[1] 黎庶昌.黎庶昌全集:2[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2] 张裕钊.张裕钊诗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3] 凌惕安.清代贵州名贤像传[M].清代传记丛刊:综录类:12.台北:明文书局,1985.
[4] 黄万机.郑珍世界观初探[J].贵州文史丛刊,1987(1):37-43.
[5] 施吉瑞.郑珍与中国现代性的起源[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
[6] 郑同知.敕授文林郎征君显考子尹府君行述[M]//巢经巢诗钞注释.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
[7] 郑珍.郑珍全集:6[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8] 黄万机.莫友芝评传[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
[9] 莫友芝.莫友芝日记[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
[10] 张伯行.学规类编:丛书集成初编:678[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11] 莫友芝.莫友芝全集:6[M].北京:中华书局,2017.
[12] 莫友芝.莫友芝全集:7[M].北京:中华书局,2017.
[13] 黎恺.教余教子录[M]//黎庶昌全集: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前言.
[14] 莫友芝.莫友芝全集:8[M].北京:中华书局,2017.
[15] 黎庶昌:黎庶昌全集:1[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16] 郭康松.清代考据学研究[M].武汉:崇文书局,2003.
[17] 郑珍.郑珍全集:1[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18] 陈奇.陈奇文集[M].北京:团结出版社,2017.
[19] 莫友芝.莫友芝全集:1[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20] 黎铎.沙滩文化概念的思考[J].教育文化论坛,2010(2):110-114.
[21] 黄万机.沙滩文化研究文集[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11.
[22] 徐钰.论清代“西南巨儒”郑珍的宋学取向[J].教育文化论坛,2016(4):121-128.
[23] 平翰,等.道光遵义府志[M]//郑珍,莫友芝,纂.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33.成都:巴蜀书社,2006.
[24] 张昭军.清代理学史:下[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7.
[25] 李朝阳.论莫友芝诗歌的艺术特色[J].铜仁学院学报,2017(8):62-66.
[26]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7] 张寿安.打破道统重建学统清代学术思想史的一个新观察[J].中国文化,2010(2):4-33.
[28] 史革新.晚清理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注释:
1 如黄万机《沙滩文化论》《郑珍世界观初探》等论文,认为程朱理学是郑珍和沙滩文化学术的哲学基础,其《郑珍评传》(巴蜀书社,1989年)述列郑珍早年从事程朱之学等事;又如张新民《经学视域下贵州学术思想的流变》(《当代贵州》2013年第10期)认为贵州清代朴学亦有来源于清中期之理学者;黎铎《沙滩文化概念的思考》(《教育文化论坛》2010年第2期)认为黎氏家族始终坚守程朱理学的“敬恕”论,强调个体人格的至善;徐钰《论清代“西南巨儒”郑珍的宋学取向》(《教育文化论坛》2016年第4期)梳理了郑珍学术中的汉、宋关系,间及黎恂、莫与俦,尤其是杨园学与郑珍的关系。
图文收集与编发:中国文化书院(阳明文化研究院)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 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