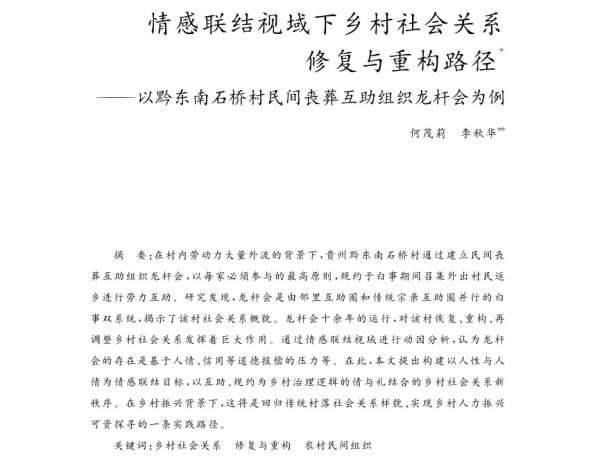
摘要:在村内劳动力大量外流的背景下,贵州黔东南石桥村通过建立民间丧葬互助组织龙杆会,以每家必须参与的最高原则,规约于白事期间召集外出村民返乡进行劳力互助。研究发现,龙杆会是由邻里互助圈和传统宗亲互助圈并行的白事双系统,揭示了该村社会关系概貌。龙杆会十余年的运行,对该村恢复、重构、再调整乡村社会关系发挥着巨大作用。通过情感联结视域进行动因分析,认为龙杆会的存在是基于人情、信用等道德报偿的压力等。在此,本文提出构建以人性与人情为情感联结目标,以互助、规约为乡村治理逻辑的情与礼结合的乡村社会关系新秩序。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这将是回归传统村落社会关系样貌、实现乡村人力振兴可资探寻的一条实践路径。
关键词:乡村社会关系;修复与重构;农村民间组织;
作者简介:何茂莉,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教授;研究方向:民族民间文化、乡村社会。李秋华(275265334@qq.com),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化人类学。
基金:2017年度贵州大学文科重点学科及特色学科重大科研项目“文化路线·互动共生:贵州地域文化生态研究”(项目批准号:GDZT20171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关于民间组织的定义,行政和法律将其认定为非政府组织,突出其非官方性质,包括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两大类。其中,社会团体是指中国公民根据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民办非企业是指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
学术界对民间组织的概念尚未达成统一意见,最常见的是把民间组织等同于非营利组织或非政府组织,如邓国胜等人就持此意见。1 学者们尽管使用称呼不同,但他们在民间组织应具备的基本特征上观点较一致,即认为民间组织应具有非政府性、非营利性、自主性、自(志)愿性、组织性等特点。2
从现有研究看,民间组织的研究探讨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环境密切相关。具体而言,我国对于农村民间组织的探讨始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当时我国正开始实施单位制改革。21世纪初,三农问题成为国家关注的重点和热点,当时多从概念界定、分类与特征、民间组织与其社会背景、民间组织与社会的关系等方面进行研究。3 发展至今,在人类学领域:一方面,针对农村民间组织的研究仍然缺乏足够关注;另一方面,从农村民间组织进行乡村社会关系研究的也相对较少,且理论范式大多离不开费孝通差序格局理论、阎云翔礼物流动相关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等,多从工具性、理性角度进行理论分析。目前,学界尚未从情感联结视域,以农村民间组织为依托进行乡村社会关系分析。基于以上现实,本文试图从情感联结视域,对贵州省黔东南州丹寨县石桥村民间互助组织龙杆会展开乡村社会关系研究。
诚如徐晓军所说:“大多数研究者都赞同,中国人的行为方式是关系取向的。”4 王庆明等认为:“中国乡村亲属关系网络的建构和再生产,所谓‘亲不亲’关键要看‘走得近不近’;‘亲’不单取决于正式的以血缘或姻亲关系为基础的‘亲疏’,亦取决于互惠性的亲属实践、频繁的礼物流动和人情往来造成的彼此认可的关系‘远近’。”5 而对于互惠性乡邻关系的体现,正如王铭铭所说:“在诸如丧事一类的家事中,帮忙操办重大家事、仪式的阵容,表现的是民间互助圈子基本的概貌。”6 在论文研究案例石桥社区的丧礼场域,本处于外圈,以村民小组为单位的民间组织关系所发挥的情感慰藉、组织劳力等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处于内圈的宗族关系,进而揭示了当今农村人情互助圈的社会互动关系。
一、石桥村龙杆会生境
(一) 自然生境
石桥村位于东经107°85′13″,北纬26°39′622″,平均海拔约为750米。1月均温5.4℃,7月均温23.9℃,年均温15.5℃。年降水量为1256.7—1458.3毫米,属亚热带季风性温湿气候。低中山宽谷地貌,山峦重叠,切割较深,地面起伏较大。土壤多为黄壤、水稻土及黑色石灰土。石桥村面积9.85平方公里,耕地面积677亩,林地面积7552亩,森林覆盖率约51%。山上盛产杉、松、构树等重要木材,出产李子、梨子、杨梅、猕猴桃等水果。7
(二) 社会文化生境
石桥村属贵州省黔东南州丹寨县南皋乡管辖,全村共331户,总人口为1363人,少数民族1170人,占总人口的85.8%。王姓为石桥村最大姓氏,共197户,占比达59.5%。8 石桥村的主要生计方式为山地稻作耕地,整体田土稀少破碎,人均耕地大多不足一亩,以水稻、玉米、马铃薯等为主要农作物。近年来,随着古法造纸业与相关旅游服务业的兴起,村内经营古法造纸及相关旅游服务业的人家达50余户。
石桥村下辖4个自然寨,6个村民小组。由于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笔者根据当地人认知,将石桥村分为石桥社区、大簸箕寨社区两个社区结构。
第一,石桥社区。
石桥社区由以行政办公、古法造纸旅游为中心的石桥堡大寨,旅游移民迁移地的新村和荒寨等三个自然寨组成。2018年该社区共计208户,848人,人口占整村人口的62.2%。其中,石桥社区非王姓户数占该社区总户数的59.4%。外出务工人数为172人,占当年外出务工人数的61%。9 石桥社区是一个移民式、开放式社区。石桥社区由于民国时期造纸业发展兴旺、可接受外来住户定居等原因,湖北、湖南、江西等地共18个非王姓外来人口逐渐入住石桥社区,因此该地居民非亲属关系居多。“石桥交通是先通的,那时候造纸挑纸去卖,人思想开放,跟外界接触多。”10 近年来,在古法造纸旅游的带动下,该社区旅游业的商业氛围较为浓郁,社区整体分布亦较松散,村民与外界接触更为频繁,也相对较为开放。
第二,大簸箕苗族社区。
大簸箕苗族社区即大簸箕自然寨,位于石桥村东部,距离石桥社区核心村委会约1公里。大簸箕一词的苗语表达为“别鸡”,意为杉树坡上的寨子。因其居住在小山包上,聚落分布远观呈扇形结构,状似簸箕,故名“大簸箕”。大簸箕苗寨共121户,其中王姓118户,占总户数的97.5%,王氏家族是一个世居氏族,系苗族。11 大簸箕苗寨因三面环水、隔河而居的天然地形地势,形成与石桥社区相区隔的独立社区空间。此外,苗寨内房屋修建密度极高,居住空间距离上的紧密进一步强化了寨内人际互动网络的联系。与石桥社区不同,大簸箕苗寨不经营造纸业,主要生计方式仍为山地稻作耕地。2000年后,随着打工热潮的来临,大簸箕苗寨外出务工人员逐渐增多。2018年外出务工人数为109人,占当年外出务工人数的39%。12 在族缘、地缘和业缘等联系仍然较为紧密的情况下,大簸箕寨社区至今依旧保持着相对稳固的团结力与凝聚力,较好地活态传承了苗族传统文化。
两社区在村民认知中存在心理分界——人们会说“石桥是石桥,大簸箕是大簸箕”。双方虽距离较近,互有往来,但约定俗成不到对方处过夜。大簸箕苗族社区不接受非王姓男子入住,传说会带来全寨灾祸、不生育等。一个村子形成了两个文化与权力中心。
(三) 石桥村白事互助系统的起源、破裂与重构
1. 传统丧葬观念导致仪式经济负担过重,产生宗亲互助传统
石桥村苗族的丧葬仪式全过程可长达月余,只有在这一系列完整的仪式结束后,在苗族生命观中才认为这位逝者已经离世,走完了人生。仪式包括:送终、报丧、测算安葬日子、停尸守灵、吊丧拢客(宴请宾客)、上山出殡、入殓、安葬、送水(送“诀别水”或称“喊魂”,与逝者告别,告知其已去世)、走客(逝者继承人代替逝者吃酒与赶场)、全村人打平伙“吃甜酒”(各家回请主人家)等。
其中,拢客开酒席、守灵的费用最高。宴请客人通常少则40桌,多可达百余桌,大多必须杀猪、杀牛等。在守灵方面,通常需要为守夜人准备夜宵,开支每晚便可达上千元。唢呐吹奏表演、跳芦笙的队伍几天不等的表演花费也均在千元以上。对于农村家庭来说,这些经济负担无疑是沉重的。因此,在成立龙杆会之前,石桥村的白事是在榔头的主持下由宗亲自发承担丧礼各环节的运作,通过串寨子、吹哨子来互相帮忙白事,以节省人力开支,久而久之,逐渐形成丧事宗亲互助的传统。
2. 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村人口外流,传统丧葬宗亲互助系统破裂
在过去,村内基本以务农为生,人口向外流动并不多。2000年后,乡村精英、乡村劳动力相继外出务工。石桥村村委会资料显示,2018年石桥村外出务工人数为281人,占总人口的20.6%。仪式主持工作者的缺乏及每家能做力气活的男性劳动力的外流,加之丧礼的操办本就较为敏感,种种因素综合下来,村内丧礼操办不仅场面冷清,送礼金额也不足以支撑主人家丧礼正常运行,导致村寨内外的人情往来越来越淡薄。因此,社区内白事服务劳动力不足,亟须规约各户、保障白事正常运行的组织及制度出现。
3. 重建白事互助系统,成立丧葬互助组织龙杆会
由于石桥社区经营造纸业,外来非同姓住户众多,各户间非宗亲关系居多,不便于协作开展白事活动,故为了增进做白事间村民的互来互往,加强村寨团结,维护村寨人情往来,2008年经石桥村村民大会商议同意后,在借鉴他村类似组织的基础上,龙杆会正式成立。当时,按石桥社区五个生产队的规制,成立石桥社区总龙杆会,并发布了相关组织章程。随后,大簸箕苗寨社区借鉴石桥社区的做法,也成立了自己的龙杆会组织。
二、 石桥村龙杆会的组织现状
石桥村现有五个小组龙杆会组织,各组具体做法略有不同,苗汉丧葬风俗各异。由于苗族占村子整体人口过半,且在白事风俗上对外来人口影响较深,因此此处以石桥社区村民小组四组龙杆会苗族白事做法为具体案例呈述。
(一) 组织结构
在参与成员方面。石桥村范围内每户默认至少一名劳动力为该村民小组龙杆会成员。该组遇丧期间,每家保证至少有一名劳动力参与白事各项服务工作,并号召所有在家的村民尽量参与白事工作。
在领导班子方面。龙杆会组长通常为该村民小组组长,其下设负责人两至三名,称为“内总”“外总”。“内总”对内,负责协调、对接主人家部分;“外总”对外,负责管辖、监督后勤保障部分。二者均通过白事时龙杆会组内开会临时选举担任。“内总”一般选举在村民小组内有一定能力的人担任,需要会做预算,对小组成员较为熟悉,识人广;“外总”大多选举村民小组长或具备一定威望的人担任,需要具备调动、管理人员的公信力。
在组织结构方面。成立之初,石桥社区一个总龙杆会组织,大簸箕苗寨社区一个龙杆会组织。后来,由于石桥社区总龙杆会组织结构过于松散、人数过于庞大、不便协作、各村民小组积极性不一等,随即按村民小组的现行行政编组进行拆分,形成石桥社区管辖的一至四村民小组等四个小组龙杆会组织,大簸箕苗寨社区管辖的五至六村民小组仍保持同一个组织,合计五个龙杆会组织。
(二) 组织分工
1. 工种
按白事的流程,工种主要分为对主人家内部、对外后勤保障两个部分。对内由“内总”负责,工作包括迎接招呼宾客、收礼记账等;对外由“外总”负责,工作包括捡拾柴火、收拾厨房、用具借还、打杂、守夜、抬人出殡、砌坟等。由于石桥村常年在家的男性劳动力不足,除当白事组主要负责以上工作外,抬人上山、砌坟等重劳力工作还需协调石桥社区其他村民小组的男丁共同协作。
2. “内外总”工作职责
在龙杆会实际运作期间,“内总”“外总”需要监督各工种的运行情况,若有工作不积极的人,则通知该工种的分管负责人进行督促。起初,在个别重要活动时还须以多次点名、罚款等形式进行严格监督,在龙杆会发展十余年后,现大多数成员的主动性、自觉性较高,基本已取消较为严格的监督方式。但对不参与、不配合龙杆会制度的人,村民也都心照不宣地不出席、不帮忙该户的丧礼,这在石桥村是最高形式的精神处罚。
(三) 运行机制
1. 丧事通知与安排分工
遇丧期间,白事主人家第一时间通知该村民小组长,到位的组长联系该组龙杆会成员开会商议“内总”“外总”人选,并由其依据组员情况拟定具体分工名单,将所有职位列于大红纸上张贴于外,此时安排何人于何职,任何人不得抗拒。待主人家把停放死者等事务整理好后,以放炮三声通知全村家中遇丧。接着,“内总”“外总”将以移动喇叭、电话、村民小组微信群等形式进行逐户通知。
2. “外总”负责的白事后勤管理工作
厨房。由于白事宴客人数较多,负责做饭的厨房是最为忙碌的一环节。即使宾客较少,如40桌等,也需要40人左右的龙杆会成员进行露天大厨房劳作,因而这方面龙杆会小组成员间采取轮流负责制。轮到该组成员做饭时,安排以家庭为单位,早中晚换班,用大蒸子轮流煮饭,必须都煮过才轮到下一轮。通常洗菜、洗碗、装酒、摆桌、端菜等轻巧活由妇女做,而苗族白席必须要煮猪肉吃,因此抬猪、杀猪、切肉、炒大锅菜等力气活由男子负责。
用具借还。每个小组都需集资购买厨具,若厨具损坏,白事主人家需付100—200元以购置新厨具。此外,小组成员每家均需募捐一套桌子板凳,如两张大桌、四条长板凳。由于厨具数量庞大,如碗可达1000多个,因此每次活动安排专人点数,由白事的主人家付其100元。
捡拾柴火。起初,各户均要从山上捡拾80斤干柴用以煮饭,较为严格的龙杆会还需要过秤检查,现可用40元柴火费代替。
停尸守夜、煮夜宵。守夜的分工安排需根据主人家停尸时长进行,此时长需由鬼师看日子进行测算,通常两至五天不等。若只停两夜,该组全体共同守夜;若停三夜,则该组均分为两队人进行守夜;若四夜,则该组均分三队进行守夜;以此类推。其中有一夜是拢客请宴的当晚,则近乎主人家和其家亲戚守。夜晚需要开夜宵,当值守夜人负责烹饪夜宵,全体龙杆会成员与主人家可同吃共话,非当值守夜人夜宵结束即可离开,当值守夜人直至第二天早上8点方才守夜完毕。
抬上山出殡、砌坟。分工到抬逝者上山埋葬的龙杆会男子们将逝者落棺、合棺,将棺材用龙杆和粗绳系好,抬棺材上山;龙杆会其他成员沿途放鞭炮,主人家亲友们随后陪同。抬到半途,需要停下棺材,等待主人家请的跳芦笙队伍进行表演。同时,龙杆会成员开始分散地抛撒小零食,作为对送逝者的客人们的犒劳。如此跳完芦笙,龙杆会抬人男子又将龙杆重新拴上,继续抬棺材上山。行至坟墓处,待鬼师做完仪式,龙杆会成员开始挖泥土将棺材掩埋、碓坟、砌坟,主人家则可以不用动手。
打杂。机动工作,负责摆桌子、上酒、冬天生火、抬饭等机动事务。
3. “内总”管理的“前台管家”白事工作
“内总”通常整日在村子入口的收礼处,由两三人分开记礼单,招呼来访宾客,收下并登记实物礼物、礼金,“外总”有开支需求时进行交接。白事活动后“内总”将账目与主人家进行核对,并张贴于村寨门口,以此对主人家及龙杆会活动经费使用情况做出说明。
(四) 组织规则
2008年,石桥社区总龙杆会成立之时一同通过了组织规则,后在执行中每组根据实际情况有所调整,以下为颁布规则的主体部分。
集资。在原龙杆会成立初期,逢白事活动每户需出干柴,现改为每户集资柴火费,由“外总”统一交给主人家用以买煤。现每年缴纳1500元左右的会费。
送礼。在成立初期,龙杆会规定红白喜事一家要送10块钱、1升(4斤)白米(籼米)。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送礼数额已不做具体规定,通常为50元以上至百元不等。
分工。在石桥社区总龙杆会时期,该组若有白事,则该组人员负责“外总”厨房部分,其他组负责守夜、抬老人上山等。石桥社区总龙杆会拆分后,则按该组“外总”安排决定组内成员具体分工。
点名制度。在石桥社区总龙杆会时期,曾执行过点名罚款制度,罚款归龙杆会所有,用于购买龙杆会用具。对重要活动分时段点名三次,确有特殊情况,可向组长请假。如守夜时,分时段点名三次,每次不到者罚50元,最高罚150元。又如抬逝者上山前点名一次,抬上山后点名一次,埋葬逝者后再次点名,不到者一次性扣钱100元。现已根据各组情况灵活管理,部分已终止点名制度。
用具管理。各户凑钱购买白喜用具(锅瓢碗盏、抬人的粗绳等等),集中放置于该龙杆会组织某户成员的闲置房间中,大多免费储存或付少许电费。
对不参与者的处罚。若家中确无劳动力能参与组织活动,可请他人代替参与。而对于完全不参与活动的人家,即不到场、不请他人代替以及不缴纳会费、罚款等情形的,给予该户红白喜事全村人均不予帮忙、不出席守夜等惩罚形式。此条已纳入石桥村乡规民约。
三、边界、修复、调整、规约:龙杆会的情感型联结是传统乡村振兴的生命力
乡村建设与振兴,其内在逻辑与秩序是根基,需要汇聚各种力量,激发村民的内生动力,融合本土智慧、真实需求,回归以情与礼为社会联结的村落样貌,在乡村文化与日常生活中共同缔造乡村价值。
(一) “石桥是石桥,大簸箕是大簸箕”:在丧事运作上村民的心理分界
关于石桥村的心理分界,村民们会说“石桥是石桥,大簸箕是大簸箕”,在心里默认村子是石桥社区、大簸箕社区两个中心的社会关系结构,这一点在各自运行的丧事系统上也体现得极为明显。
一是祭祀类型界限清晰。石桥社区以家庭祭祀为单元。据本地人说,近四成的石桥王姓户,与大簸箕社区祖上曾是两兄弟,但大多早已出五服,因此只有少部分家庭需联动两个社区的王姓进行家族祭祀,并且白事联动与否还是要看现在关系“走得近不近”。除王姓外,该社区约占六成的他姓户姓氏分散,之间的白事祭祀也以家庭祭祀为主。而在大簸箕社区,祭祀则是依赖自身较单一、较亲近的王姓氏族血缘关系,维持着更为传统的王姓家族祭祀。
二是龙杆会的运作有差别。首先,因石桥社区杂姓多,在龙杆会的发起上,亟须成立社会救助式的保障组织,以规约村民,保障白事系统的正常运行。其次,石桥社区的龙杆会运作显得十分正式,规则制定具体,执行较严厉,如需要进行现金惩罚、登记、点名等。在此处,“内总”“外总”的权力也是相对较大的,“安排何人于何职,任何人不得抗拒”。对于多次不参与的人家可予以开除,对于从前未参与活动而后期想用钱加入的家庭予以坚决拒绝。此外,为加大组织执行力度,后期进一步分化为四个石桥小组龙杆会。所谓“要喊得动人”,监督、规约、惩罚,成为石桥社区龙杆会的内在运行逻辑。13
尽管大簸箕社区也成立了社区龙杆会,但后期未出现分化。其规则执行、监督,远没有前者执行严厉,也未进行现金处罚等。“出多少人我们心里知道就行了,不用登记……石桥杂姓多,我们大簸箕都是一家人,多少都有点亲戚关系的。”14
可见,在丧事运行上,两个社区显示出了极大差别,即以规约制度、组织化构建的互助型邻里圈和“一家人”式的传统宗亲互助圈,二者“一直各做各的”,共同形成了石桥村白事运行的并行双系统。在人生重大节点上,其社会秩序的运行逻辑向我们揭示了石桥村社会关系系统的图示与概貌。
(二) “我们都是一个村嘞嘛”:龙杆会对礼尚往来的传统乡土社会关系的修复
胡必亮从中国传统社会关系出发,认为中国村庄是一种关系共同体。15 在石桥村两个社区间,存在着一种似亲非亲、似邻似友的微妙社会关系,礼尚往来的人情是这种社会关系的主要表现方式。黄光国认为“人情”的含义可以代表一种有来有往的社会交往规范。16 在过去,石桥村白事操办曾难以为继、入不敷出。龙杆会的出现,强制规约每家村民必须有人参与白事互助,规约了村民间互相送礼的最低金额,并且承担了丧葬仪式中所有的劳力工作。强制参与、规约送礼、节约人力成本,为礼尚往来的社会关系的修复提供了现实基础。
一般而言,红白喜事时赴宴的宾客越多,越说明该主人家有面子,权力大,声望高,社会地位高,是人情练达之人。尤其对于长期在外务工的村民群体而言,能够在白事场合依旧保持传统熟人社会里的人情往来,发挥其显示声望的面子作用,就是一种为老人尽孝的体现。那么,这种以红白喜事互送礼金、相互赴宴为社交方式的人情往来便是至关重要的。如今,随着经济发展与龙杆会对村民乡土社会关系的不断修复,白事宴请的宾客规模已由龙杆会成立前的寥寥数桌,达到少则40桌,普通规模七八十桌,多可达上百桌的局面,现在亦不需再规定送礼金额。
(三) “帮还是不帮?”:劳动力外流背景下,在场与不在场群体关系的调整动因
莫斯在《礼物》中提出:“具有破坏力量的‘礼物之灵’,如果将载有这种灵力的东西送出,接收方将它留下,不给予回报,那么这种灵力将会发挥它的破坏作用,使对方生病,甚至丧命,所以这种灵力使赠礼尤其是回礼成为一种义务,这种义务形成了永不间断的赠礼—收礼—回礼的链条,维系着古式社会。”17
对于外出务工的人群而言,确有事无法返乡参与活动时,可按龙杆会章程规定,请在场的他人代替其参与活动。这种代替帮人的人情,可被视为一份厚重的恩情,成为一种道德义务将双方永远联系在一起,表面上看是自愿的、自发的,背后却隐藏着道德上的义务性和强制性回报的压力。在进行人情回馈后,双方私人关系乃至双方家庭关系大多都将得到极大提升,至少私人关系能够得以维系。若仅是受龙杆会的帮助,而拒绝付出劳力,则会承受整个村子的非议,被认为不讲信用、为人差,从而彻底断失人际关系网络。帮忙与否,从道德义务角度上强制厘清了双方的社交边界,乡村社会关系网络由此得到重新调整。
此外,是否帮忙,除了组织规约义理道德的约束外,还有出于私人关系上的情感考量,以及社会资本的理性考量。阎云翔18认为从施助者角度看,其决定付出劳动往往基于以下两个情形:一是对方的人品、声誉值得信任,以便于将来会来帮忙自家白事;二是对方是有能力偿还人情的人。
(四) “远亲不如近邻哩”:乡村振兴背景下,构建情感型、互助式情与礼乡村社会关系新秩序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的一般要求。乡村产业建设所需要的人力资源,乡风建设中对传统乡村优秀文化的坚守,不仅需要经济吸引力由城返村的转移,还内在地要求以人性、人情为情感联结、乡规民约为礼治约束的传统村落样貌的回归。
情感型传统乡土社会关系的重塑。传统乡土社会的人类关系共同体,尤为体现在生命结点时守望相助的终极人性关怀,它们形成了村民们割舍不开的、盘根错节的乡土社会关系的心理依赖。村民们通过在丧礼场景相遇、重逢、共同劳作、全程观礼,重温了关于村落丧葬文化的集体记忆。尤其是在守夜环节,每家须至少有一名龙杆会成员参与轮流值守。自发守夜或安排到场的人愈多,愈说明群体的关心与情感支持。主人家亦会对参加守夜的人表示十分感激,热情款待夜宵。在守夜场景下,新继承人与龙杆会成员们彻夜攀谈,一方面得到了情绪上的镇定与安慰,另一方面增进了双方的了解,新继承人也得到群体认可。其间,对逝者的郑重缅怀、村邻对失亲家庭的同理心、共同协作的凝聚力、对应对未知生活的共同信念等,形成了对孝文化、生命观文化、互帮互助的人情文化等村落文化的价值认同,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村落社会文化空间与价值认同的精神文化家园。在组织运作下,人们将村民身份进行重新确认,使生者重新结成整体,修复与乡土群体关系的情感联结。
同时,当城市商业的金钱逻辑与乡土社会的人情逻辑相碰撞时,回归传统人情的乡村面貌成为村民的内心诉求。在今天的乡土社会中,本人亲自到场吃酒,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比送大额礼金更加表达了对对方的重视,并且对方也会感受到这份情谊,将来也愿意到场以归还这份人情。两边都吃酒的WQH校长是个典型案例:
南皋中学的第一任校长WQH是石桥村大簸箕苗寨人,为人较为开明,与石桥社区的私人关系也较为良好。石桥社区人家的红白喜事,尽管他没有亲戚关系,但都会去参与吃酒。所以在他家做红白喜事时,基本全村都到场,守夜人数达历来最多,提起他大家都是尊敬的。19
构建互助式礼治规约乡村社会发展路径。现有龙杆会是在以村民小组为单元的社会关系网络基础上运行的,组织内大部分村民间呈非亲属关系,处于差序格局波纹中心的外层。尤其对于长期在外务工的农民工群体而言,在关系到如收礼、入殓等较为敏感的环节时,正是这样一个组织及规定,赋予了组织成员相关责任、义务,这些位于差序格局外围的村邻关系身份才不会显得越界、尴尬,做事也会变得积极得力。通过强制性召集远亲甚至无血缘关系的村民,大家在生命仪式实践过程中协同一心,共同应对生命无常的风险。类似龙杆会这样互助式民间丧葬组织的建立与运行,既是一种朴素的民间生存智慧,也体现了当代乡村呼唤回归传统人情社会关系的真实需求。应对该类组织加强研究与保护,探索一条以增进村民情感联结为目标,以乡规民约为实施保障,以村民心理边界为单位,以村民人力互助为实施手段的情与礼结合的乡村社会关系新秩序,从而为乡村人力振兴提供策略。
四、结论
本文以贵州省黔东南州丹寨县石桥村民间丧葬互助组织龙杆会为例,从该组织的起源生境、组织现状进行描述,并从情感联结视域具体分析该类组织对传统乡村社会关系的修复与重构路径。笔者认为,在农村劳动力频繁流动、宗亲关系地位日渐式微、乡村白事人情往来逐渐淡薄的背景下,亟须建立并长期运行该类民间丧葬互助组织。它以“村内每家人必须强制参与,否则全村不出席该户白事”的最高原则,维系着乡村传统生命仪式的庄重与完整;以村民社会关系的心理分界为单位,通过丧礼场域的劳力互助、情感慰藉,抵消因人口外流造成的对村落传统文化与传统乡村社会关系的削蚀。白事宴客规模全然恢复甚至更为兴盛,乡村人情走动也逐渐恢复生机。对此中动因的分析上,笔者认为在情感视角,是基于对该类组织所带来人情、信用等道德报偿的压力、村规民约的义理约束,以及对私人关系、远近亲疏等的考量;在理性视角,则是出于对社会资本等因素的考虑:在以上因素的综合考虑下,如今乡土社会关系得到不断的调适、变动。在此分析之上,笔者提出构建以人性与人情为情感联结目标,以互助式、规约式为乡村治理逻辑的情与礼结合的乡村社会关系新秩序。
在农村人口向外流动、村民对乡土归属感逐步下滑的当前语境下,民间互助组织的存在与长期运行,既反映了在场与不在场村民试图邻里合作、互通人情的愿望,也反映了对乡土群体关系的依赖和对联结乡村社会关系的真实诉求。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了解该类组织对乡土社会关系的重要调节作用,对于有效调动和发挥民间生存智慧、保护这类地方性乡土资源、形成团结互助的文明乡风、实现乡村人力振兴不无裨益。但从长远看来,龙杆会要保持其良性运作,仍有资金、人员、场地等问题亟待解决。这就需要社会各界对龙杆会这样的民间互助组织产生的良好效应及作用予以重视,并采取适当引导和保护措施,使其产生更大助益。
注释
1 邓国胜:《非营利组织评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2 王名、贾西津:《中国NGO的发展分析》,《管理世界》2002年第8期,第154—155页。
3 万江红、张翠娥:《近十年我国民间组织研究综述》,《江汉论坛》2004年第8期,第123—125页。
4 徐晓军:《内核—外围:传统乡土社会关系结构的变动——以鄂东乡村艾滋病人社会关系重构为例》,《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24期,第244页。
5 王庆明、王朝阳:《人情冷暖与亲属实践——中国乡村婚姻困境的一种解释》,《开放时代》2019年第2期,第8页。
6 王铭铭:《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闽台三村五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97页。
7 参见“丹寨县南皋乡石桥村2018年基本情况数据统计表”等。
8 参见“丹寨县南皋乡石桥村2018年基本情况数据统计表”等。
9 2018年,石桥村一组至四组共202户,其中王姓户数为82户,杨、罗、张、文、李、吴、熊、龙、莫、曾、陆、梅、刘、余、蔡、梁、孔、潘等18个非王姓户数为120户。
10 报道人LGW,苗族人,1986年生。访谈地点:石桥村荒寨。访谈时间:2019年10月11日。
11 参见“丹寨县南皋乡石桥村2018年基本情况数据统计表”等。
12 参见“丹寨县南皋乡石桥村2018年基本情况数据统计表”等。
13 报道人LDP,苗族人,1982年生。访谈地点:石桥村荒寨。访谈时间:2020年9月7日。LDP:“加入小组龙杆会是收会费的,因为有些人家刚开始做会时他们没在家,人也勤快,后加入大家也不会多收。有些人家太懒或多次缺席被开除,想要加入别的组给再多钱人家也不接受。现在我们石桥也只有几家没参加了,现在想要加入,哪一组都不要。”
14 报道人WXZ,苗族人,1982年生。访谈地点:石桥村荒寨。访谈时间:2020年1月5日。
15 胡必亮:《关系共同体》,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2页。
16 黄光国、胡先缙:《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领导文萃》2005年第7期,第162—166页。
17 马赛尔·莫斯:《论馈赠:传统社会的交换形式及其功能》,卢汇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页。
18 阎云翔:《差序格局与中国文化的等级观》,《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4期,第245—246页。
19 报道人LGW,苗族人,1986年生。访谈地点:石桥村荒寨。访谈时间:2019年10月11日。
原载:《宏德学刊》2022年02期 第十五辑 第265-277页
编发:中国文化书院(阳明文化研究院)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 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