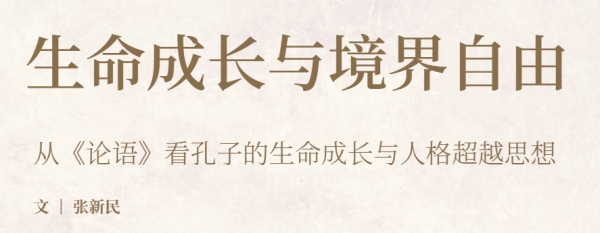
编者按 2023年9月28日,时值孔子诞辰2574年,亲民之道公众号特别刊发张新民先生文章《生命成长与境界自由 ——从<论语>看孔子的生命成长与人格超越思想》,致敬至圣先师。
《论语·为政》有这样几句话: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1]
此为孔子自述其生命成长与人格完成漫长之心路历程, 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历来皆是人们重视精神修养提升生命境界的源头活水重要性“象征”资源。尽管每个人的生命成长与人格完成有其个别实例的特殊发展的例外,但孔子之“言”与“行”作为“历史原型”或“人格原型”的感召性“象征”,一经汇入整个文化传统的生命之流中,就时时处处都能透过多数人的实践, 显示出生动普遍的范型意义和精神价值。后世每喜引孔子之言作为自己年龄阶段与境界成就的代名词, 即可从中窥见其话语的历史份量与自觉认同的心理力量。盖表面简单的语句下,蕴涵了强烈的生命成长的实践与要求;在人生奋勉的理想下,含藏着深刻的形上意义的期盼和关怀。
犹如佛教以为菩萨由初发心到成佛,须经历五十二位或三大师阿僧祗劫漫长历程一样,儒家也认为由立志到进入“圆善”“自由”的境界, 乃是一终生持续不断的艰苦过程。境界的升进与人格的达成,在于时时处处当下的奋勉,而时时处处当下的奋勉,即是“生命局限”的不断突破与“生命质素”的不断提升。孔子的“言说”表明了中国文化对生命成长的关注和信心,代表了东方传统对生命本质的悟觉与智慧,是生命能彻入“圆善”境界、“自由”境界的具体亲证,不仅在理念上关系中国“成学”传统极大,而且在实践中也带动了大批贤哲之士的涌现。
一、生命意义的终极承诺:十五志于学
孔子言生命之成长,始于十五“志学”,乃是把建立自己的志向,当成朝向终极意义的人生的开始。建立志向不能没有“理念”,按照韦伯社会学的分析,正是“理念”所创造的“世界图像”,决定了人生轨道的价值发展方向,尽管推动人类在轨道上前行的原因极其复杂,但由价值构筑而成的轨道的范导作用仍决不可轻忽。可见“志向”就是理念导引的人生方向,无理念导引的人生,必然如无航的帆舟,脱缰之野马,四处漂荡奔逸,茫然不知底所。所以儒家以立志为生命之首要,即是因为透过志向所持的内在理念,我们才能清楚自觉人生的“图像”;只有心志广大清明,人生才有追寻的目标,才能肩任宏远大道。而也只有跋涉于生命成长的“大道”上,我们才能最终寻到安身立命的“精神之所”。
儒家关注生命意义的创造与人生价值的实现, 孔子所说“志于学”的“学”,主要亦不是现代所说的知识系统, 乃是“志于道”(《述而》),即“朝闻道, 夕死可矣”之“道”(《里仁》)。这里的“道”当是提升精神境界的真理, 生命实现的真谛, 是每一个体都可通过道德践履来亲证的境界。孔子感慨:“有颜回者,好学, 不迁怒, 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雍也》)志于“道”即志于代表真理的“大道”,是必须凭借道德大勇才能作出的存在抉择。因为人总是就其发展的可能性来决定人生方向的,“志”愈高远而风险愈大,好者从者亦必愈少。而依照韦伯之说,决定人生轨道方向的关键,虽是与“理念”或“志向”相关的个人“世界图像”,但支配推动人类行为的, 更多地则是物质与精神上的利益,精神利益之追求亦为人类永远之必需。儒家则不仅关注人类的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而且要超越这一切利益,以代表人类的永恒价值为理想人格,以万世太平的最终实现为目的诉求。真正的道德行为只能是透过严格意义上的义利之辨,不断地迈向终极堙想境域的依“义”而行的实践化人生抉择行为。

因此,孔门理想人格要求下的立志,与一般意义上的对事物的选择不同,乃是存在的根本性抉择。存在的根本性抉择之为抉择,在于说“是”的同时说“不”——有所为有所不为。一方面在抉择中获得了自由与超越,不能不是自由意忘与道德法则互涵下的主体自我行为,是无条件的依埋而行并当行而仃的人生目我实践;另方面也在选择中承担起责任与磨难,必须具备孤往直前的道德大勇,拥有安贫乐道的牺牲精神,―切都以道德心灵的满足与实现为根本前提。此非少数高义洁行、独立卓绝之士, 即难做到,故孔子曾慨叹“好学”之士太少,并反复强调“士志于道, 而耻恶衣恶食者, 未足与议也”(《里仁》);“君子谋道不谋食”(《卫灵公》);“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这是立乎其大,小不能夺的结果。而以自利自私为学者,其心志先已卑陋,其智量原已狭小, 既无“志于道”之形上关怀与践履要求, 当然就无法理解生命成长直趋之高胜境界,感受不到存在抉择取舍之间的无限庄严, 更难有“守道”“行道”者一往不顾的生命充实光辉和人格伟岸挺立了。
立志是生命的内在自觉要求, 不是外在他律的行为强迫。生命成长的动力或依据, 即是人人皆可自觉的“仁心”,“仁心”透过同情心(不安、不忍)尊敬心(敬、诚)而呈现, 乃是人的内在道德本质与实践的本体依据。无“仁心”即“麻木不仁”,亦不可能真正意义上的立志,所以孔子讲“志于道”的同时,又讲“志于仁 ”( 《里仁》)。“仁心”内在, 志亦内在。“志”字着ψ从“心”,即显见它必须来源于内在的本心本愿, 体现了人的理性意志与情感意志[2]。而内在的“志”与内在的“仁”显然也一样,本质上是自由、自主、自律和不可剥夺的,因而也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的(《子罕》)。“志”作为主体的自我选择, 生命的自觉主宰,其最高境界乃是与“道”、“仁”合一的境界,亦即本体存在的境界——生活在“道”的世界,“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 颠沛必于是”(《里仁》)。而一旦“道”的本体世界与现实世界发生冲突,必要时亦敢于以身殉“道”,舍生求“仁”。“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 。“道”的绝对性、“仁”的至高性、“志”的主宰性和不可剥夺性,在这里得到了圆融化的统一和最大化的彰显。
内在的“志”或“理念”当然要显发为外在的行为。所以真正的“立志”者必然要参与历史文化的创造活动,对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价值理想有清楚的自觉和认同。这也是儒、道两家的一个重要区别。孔孟、老庄都认为生命成长的本质在于精神价值的提升和超越, 而非有质有碍的躯壳形骸的生物性或生理性成长。所不同者,老庄主张“绝仁弃义”,在历史文化之外获得精神的绝对自由,彻入与“道”或“天”合一的逍遥游的生命境界。孔孟则认为人格理想的实现可以达到精神自由,而人格理想的实现与文化理想的实现是一致的、不可分割的,立志者必须通过行“仁”履“礼”等种种社会生活的实践,创造自己的生命价值和文化理想价值,因而儒家的社会关怀和人文关怀历来都是最为突出的。孔子要弟子各言其志,于子路、颜渊之答均不甚满意,而自己的志向则是“老者安之, 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公冶长》),表现了儒家社会和人文关怀胸襟气象的博大与深厚,也决定了孔门要求的“立志”必然有深刻的承担历史使命的宗教性内容。当然,孔子对精神自由的绝对价值也是充分肯定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 游于艺”(《述而》),即清楚显示了人格发展方向的完整与全面,这就是为什么孔子要说“吾与点也”, 对曾皙的志向最为欣赏的缘故。说明儒家社会关怀之外,尚有其诗性关怀, 在积极弘扬文化理想,担当历史使命的同时, 也有不脱离现实社会或具体人生的自得理想与超越精神。儒学“立志”的根本理念在有情而不为情所累,转世而不为世所转——既要参予历史文化的创造性实践活动,又始终对人的“异化”行为保持警惕;既“心忧天下”, 又“乐天知命”;既经历入世的苦难磨励,又满含出世的乐观洒脱。正是在转世(改造现实社会、改造现实人生、创造历史文化、建构和谐秩序 )而不被世传(志向不可剥夺,人格不可剥夺;不为物役,亦不为人役) 的伟大人文事业中,人体悟了生命成长的意义,契入了人生本真的本体论存在境界。正是在这一意义上, 也可说“志于学”即志于“人文学”,志于从每一个体到人类整体合理存在、和谐生存这一最伟大的人文发展创造事业。

儒学终极关怀意义上的“立志”,既立足于内在精神天地自我修养的不断升进和发展,也关注外部世界文化理想的实现与达致,要求内外贯通合一,形上形下不即不离。儒家当然也有自己的知性诉求或知识关怀, 孔子“志于学”之“学”也包含了历史遗产的学习, 但“下学”是为了“上达”, “上达”乜有必要“下贯”,形下”“形上”一样要浃然互通。此即内圣外王之道、天人合一之道。有志于实现这种内、外、上、下合一贯通的即整体即本体的精神境界,人自然会涌现出勇猛开拓、无限上进的力量, 产生刚毅超拔、坚忍负重的气慨。孔子说自己“发奋忘食, 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述而》);曾子亦自勉云:“士不可以不弘毅, 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 不亦重乎? 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泰伯》)这是立足于终极关怀而产生的巨大精神创进力量, 是终极承诺赋予的沉重历史责任。同耶稣上十字架,苏格拉底赴死刑,释迦牟尼主动肩荷人类苦难一样,孔子也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生命大勇,超拔挺立于人类历史文化之上,成为轴心时代永世不磨的价值活泉与象征符号。儒家生命成长的思想,从生命朝向终极意义的“立志”开始, 就带有崇高的人生责任和远大的使命色彩, 表现出深刻的“宗教性”道德修养的内涵。当然,“立志”只是对终极目的有所承诺, 具体实现则需要终生的奋勉和一刻不停的磨炼。
由此可见,“立志”为儒家“宗教性”道德修养的关键和根本, 也是“内圣之学”终极目标及终极承诺的出发点。熊十力先生对此体悟颇深,他说:“余以为志, 天人之枢纽,天而不致流于物化者,志为之也。志不立, 则人之于天,直是枢断纽绝,将成乎顽物,何复其天乎?”他认为“此则吾平生亲切经验之言,垂老而益识之明,持之坚也。此枢纽树不起,则毋自欺不能,毋自欺作不到,而言涵养操存,其不陷于恶者鲜矣。”[3] 立志作为人生自我的终极承诺,不仅提供了人格或道德挺立的力量资源, 而且直接与活泼泼的天道合流,避免下陷、自欺、疏隔、物化的存在可能,其言颇值得三复玩味,从而不断砥砺人生应有的志节与志向。
二、人格自我的建立:三十而立
“三十而立”是指生命已有了主宰性、决定性、创造性,人的内在本性的发展与外在的伦理生活已完全统一,人的主体性与自由意志己彻底建立,能够自觉地反省自己行为的是非对错并及时地判断调整。易言之,既时时处处都能遵循或践履人类共同的生活准则与普遍的社会性规范公德,又能由此而在理知及情感两方面都感到并维护自我人格的卓然挺立和生命的道德尊严。孔子说“不知礼,无以立”(《尧曰》);又说“立于礼”(《泰伯》);即显示了个人主体性的追求和高扬必然和“礼”的践履有关,“礼”既有助于生命素质的提升,也有助于人格尊严的维护。“礼”乃是人类共同生活准则与普遍社会公德的制度性架构,人正是通过生活世界的具体“礼义行为”,才建立起成熟的人格自我, 表现出生命的尊严,创造出一个与动物有别的人文化成的世界,即所谓可以安身立命的文化与文明的新天地的。
“礼”必须本于真实本然的心性, 在孔子那里就是可作为一切道德行为基础的“仁”。士之志于“道”与志于“仁”, 即是对“道”必然显现为人间价值秩序,“仁”必然发用为社会生活行为, 有一坚强之理想和信念, 而志“道”志“ 仁”的当下, 即努力实践的当下,不容一刻迟缓,不容一刻懈怠。“仁”发为社会生活中的具体行为, 就是人间活泼泼的“亲情”与“正义”, 将此“亲情”与“正义”规范化、制度化, 就是极富人世温情的“礼”或“礼制”。所以孔子说:“人而不仁, 如礼何?”(《八佾》) 这是以人为客观化的“礼制”的主体, 内涵制度必须人性化——以人为目的而不是工具的深刻意义。而“礼”之所以成为人类社会生活的必要,就在于它是人的内在“仁心”的根本呼唤与需要,同时又是天道和谐创生的基本原则的具体展现和有效落实。

文化人类学告诉我们,“礼”的起源可追溯到原始社会,而且一开始就和生命成长息息相关,几乎生命展开的每一重要过程都有相应的“礼”的仪式。在习“礼”践“礼”的过程中, 自然生理的生命逐步转化为社会文化的生命,生命铭刻了共同的文化价值,也具备了“神圣”或“道德”的意义, 肩负了责任,也享有了权利。孔门对“礼”自觉反省后,更强调“礼”的“中和”精神及其对伦理修身的作用, 即透过“礼”的“中和”精神, 调节人的行为, 规范人的情感, 使其符合自己当下伦理处境中的地位角色, 从而增强人际间的情感认同与调适顺遂,由此建立起合宜适中的人格自我,落实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否则“恭而无礼则劳, 慎而无礼则葸, 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 ( 《泰伯》) 。美好的行为缺乏“礼”的调节, 也会违背“中和”精神而流于偏至,与人文修养的圆融化境在方向上就距离了很大一层。因此, 生命素质的提高,“礼”的学习与实践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孔子言“克己复礼”,“复礼”即 “践礼”, 从十五“志学”到三十生命始有重大突破, 可见孔子认为人格的建立有一长期“践礼”的过程,“立志”的终极承诺不能脱离生活世界的日常践履,《论语》载子路问“成人”, 孔子以为尽管如“藏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 都还不够, 必须“文之以礼乐”, 始“可以成人”(《宪问》)。可见生命成长(成人)既需要“志于仁”的内在动力的自证亲觉, 也需要见于“行”的外在实践环境的熏染感化。“礼”的实质在于生命质素的提高,修养境界的达成, 只有“克己复礼”,使自己的视听言动都合乎“礼”, 行为无不发而中节, 情与理、知与行、自然与人为、理性与感性都和谐统一, 臻于高度自觉的修养境界, 才能真正建立起人格自我,亦才能“天下归仁”。当然, 生命质素的提升, 人格境界的展现, 其本身也需要“礼”的生动形式以为表现,是任何人都无法躲开或绕过的人生社会化实践环节。
作为制度化的“礼”, 其本质亦可说是集体性的。因为人处于与他人相互依存的“共在”关系中,如何避免冲突而达致和谐, 则不能不依赖于“礼”的和谐化运作。“礼”把个人与他人的生活或行为按亲疏远近联结为一整体的格局,以人人各殊的集体的规范帮助人们选择适宜的行为, 从而建构一个颇有人情温暖的“主体间性”的“世界”, 使人与人之间的“我—他”关系变为“我—你”关系,所以儒家一贯有礼治为主、法治为辅的思想,礼教的文化学意义及其内涵的人文精神在世界各国最显得突出。孔子生活的春秋之世, 正是周文疲弊, 礼乐崩坏, 人心迷乱, 文化失范的时代。孔子本其大智大勇, 从主观方面讲“仁”, 就是要从大根大本处挽救人心的蔽塞与堕落,使“礼”的架构有一道德本心、道德情感的深层存在根据;从客观方面说“礼”, 就是要重新发挥周代文制匡正社会价值秩序的功效, 使道德本心、道德情感以“礼”的形式彰显出来。儒家始终有重礼制、重秩序的强烈情结, 对经由伦理教化开出的政治制度上的治国安民极为重视, 目的也是要维护“仁”所蕴涵的“主体间性”的普遍性生命尊严, 使依于内圣之本的人格挺立能普遍具体地落实。可见人际间互相“共在”彼此尊重的“主体间性”, 亦是儒学真正意义上人格(道德)自我建立的重要内涵。所以“礼”作为集体性的制度化架构,仍然以每一个体的人格发展如实现为根本目的。
儒家通过“践礼”实现的生命成长, 也是不断参与社会生活的意义创造, 在社会中不断完成自己的生活价值的过程。三十岁时, 人格成熟已得到了社会的完全肯定, 而人格成熟必然意味着对他人生命及要求有所关注和尊重,不如此仍不足言自我价值的真正实现。这就是孔子所说“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雍也》);自己希望建立人格自我, 维护生命尊严,也帮助别人建立人格自我, 维护生命尊严;自己希望不断提高生命素质,成就理想境界,也要帮助别人提高生命素质,成就理想境界。反之,则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此即忠恕之道, 在考虑问题时, 以自身为“尺度”, 推己及人, 顾及他人甚至它物的利益, 使每一个体都调畅顺遂, 各尽其“性”, 各得其“所”。就“仁-礼”约关系结构而言, 它既是“行仁之方”, 当下即可本于人人同然之心而实践——“仁远于哉? 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同时又是“礼”之精神,当下就能履行责任义务发而中节——在“礼”的自律 ( 自由 )王国中实现人格, 在人人共在的“主体间性”的人文环境里安立生命。所以不仅一人“归仁”,而且“天下归仁”;不仅一人“立于礼”, 而且人人“立于礼”;自己的人格独立不能防害他人的人格独立,白己的自由意志不能厄及他人的自由意志,每一个体的生命尊严都以他人的生命尊严为前提,每一个体的自由意志都有裨于成就他人的自由意志,由此形成人的道德的联合体,必然也是人的自由的联合体。
三、不惑之智的证得:四十不惑
“不惑”是生命成长的又一重要新境界, 是生命意义与价值实现的必要一环。何为“不惑”? 孔子说“仁者不忧, 知者不惑, 勇者不惧”(《子罕》),可知“不惑”主要与“知”关连,“知”可训释为“智”,四十岁才成为“智者”而不惑。“智者”的人格是完整的人格,生命素质的转换提高,依赖于人格的完整,完整的人格即“仁”“知”“勇”统一的人格, 孔子以此三者为君子之“德”,表明了他的人格理想的“完整性”。与老子说“知”主要为知识认系统方面的“知识”和“智慧”不同, 孔子的“知”则更偏重于人文道德方面的“知识”与“智慧”。在“仁”的本体精神境界的弥漫笼罩下, 经过长期脚踏实地的“习礼”、 “践礼”的经验累积,对内在本然的“仁心”“仁性”及能力已有完全清楚的“自知”“自觉”, 对外在应然的人文世界及其价值根源也有了深刻的“体验”“体认”, 由此转出智慧, 生出大勇,坦坦荡荡,不忧不惧,这自然能“不惑”, 自然是“智者”——“智者之不惑”、“不惑之智者”, 既是中年时人格更加完整成熟的显著表现, 也是生命局限再次突破飞跃的重要标志。前提和保障当然仍是前面提到的少年时的“立志”, 青年时的“践礼”,尤其是自由意志的纯一开显,以及人格的卓然挺立。“不惑之智”的现前涌出与亲证亲验, 是生命继续精进不已、奋勉不息的必然结果。
“不惑之智”的证得,当然也与为己之学的修养工夫有关。在长期的“习礼”“践礼”活动中,道德主体不断地反省自我, 做“反求诸己”的工夫——“君子求诸己”,“见不贤而内省”,如孟子所说“爱人不亲, 反其仁;治人不治, 反其智;礼人不答, 反其教;行有不得者, 皆反求诸己”(《孟子·离娄上》)。不断依据行为及“心性”本体互相省察, 生命素质、生活质量必然逐步趋向提高, 久久功夫纯熟, 心性本体亦必然会有“去蔽性”的豁然洞开, 于是由心灵深处透出生命创造的智慧光明,涌出意义与价值的源头活水。这就是由本然“心体”的证悟, 再次获得生命的飞跃式重大突破。在这样的境界中, 人如何能不自立、自得, 涌出无限自信的力量呢? 如此则面对一切价值抉择, 无不有内在本体的准则为依据,有源自本真人性的理则为基础,有面对世俗万千变化,亦能不迷转于外物而自作主宰作决定,是真实主体性不期然而然的及时可靠的到场。这即是“智者不惑”的境界, 也是“本体”“工夫”收摄合一的难得人生佳境。
内在心体性体全然洞开,由此呈现出的强大理性活力,自然能知是知非,由此涌现出的活泼道德感情, 自然也能好“善”恶“恶”。“知者不惑”, 即不混淆是非, 不溺于好恶,且是非得当, 好恶得宜, 当是即是, 当非即非,当恻隐则恻隐, 当尊敬则尊敬, 无执无著, 恰到好处。如果是非累于“心”, 好恶累其“情”, 甚至执着偏至, 违背中正平和的精神, 譬如“爱之欲其生, 恶之欲其死, 既欲其生, 又欲其死”(《颜渊》), 仍然为滞于“惑暗”之中,未能进入“智慧之境”。“迷滞”“惑暗”之中的自我, 乃是尚未与真实沟通的自我, 既不能与本然的“心性”相应, 行为就难免有过或不及的偏差。“智慧之境”的“智者”, 内证自“本心”“本性”, 开出积极的“主体世界”, 外显为中和广大, 拓出广阔的“人文世界”。故“功夫”稍有所不及, 即不能臻至此境。
“不惑之智”的证得, 当然也需要相应的人文学知识。“人文学”追求的知识, 是真实的“学问知识”, 活泼泼的“真理”, 力求与外部的“真实”沟通, 彻入本体(存在 ) 的境界。“人文学”观察自然,理会人生,贵虚心忘我,优游涵泳,主要是“领会”、“体验”的方法,因此在态度上,就要“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是知也”(《为政》)。“知”在这里也可训为“领会”、“体验”。意义与价值的本体论的“领会”、“体验”, 必出于来自心源深处的诚敬,“领会”、“体验”到了就说“领会”、“体验”到了, 没有“领会”、“体验”到就承认没有“领会”、“体验”到, 这才是真正的“领会”、“体验”。在具体的实践上, 则要像孔子所说的那样,“盖有不知而作之者, 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 知之次也”(《述而》)。知识性的“人文”或“文化”, 一定要根据“择善”的标准,“毋意, 毋必, 毋固, 毋我”(《子罕》),“领会”、“体验”其意义与价值, 并化为当下生命实践的切实受用。“真知”必不期行而自行, 否则只能是“知之次也”。这里的“知”仍然是有关生命成长的“本体”的学问, 并不走向纯粹的以主客分裂为前提的知识论。人是赤裸着来到世界的,一无所有, 不能不学习“人文”或“文化”, 透过“人文”与“文化”了解人生,了解世界,契入其实的“生命”,彻入真实的“世界”,使生命成为有意义的“生命”,世界成为人的“世界”。人又是行动者、创造者, 不但能主动为“善”,也知道自己的行为合乎“善”, 在“善”的行动中为“生命”与“世界”赋予“人文”的价值和意义, 从而“生命”与“世界”同时澄明敞亮, 成为诗意的“存在”。所以真正“不惑”的“智者”, 一定是“知”而“真切笃实”,“行”而“明觉精察”,内外打通, 知行合一的。“不惑”者生活在意义与价值的“世界”中, 从事精神生活或文化的创造活动,倘于“人生”及“世界”的意义有一毫不透,于人文关怀、价值追求有一丝不明,生命实践的行动稍有迟疑不决,即是有“蔽”,即是有“惑”,无疑于“智者”的境界仍有一间未达,当然就有必要沿着早年立志的方向继续修养和不断实践。

在人文活动中展现的不惑之“智”,实际也是一种超越世俗的“生命智慧”或“精神境界”。所谓超越“世俗”,并不是不正视“世俗”的挫折艰辛和黑暗苦难, 儒家学者前赴后继,总有其社会关怀、文化忧患,即是重要的历史明证。前述孔子所要求的完整人格,必须“仁”“智”“勇”三者统一。“仁者”悲天悯人,满腔仁爱关怀, 何能无视入世苦难;而“仁者必有勇”, 儒家要积极入世,实现理念,落实理想,影响世道人心,改造社会人生,又何能没有勇气? 所以一个真正透悟人生使命的“不惑”的“智者”,一定也是满怀悲心、广施厚爱的“仁者”,同时又是“虽千万人吾亦往矣”的“勇者”(《孟子·公孙丑上》)。只是“智者”在勇猛入世,承担责任, 肩荷世间悲苦的同时,无所谓“得失”,不计较“毁誉”,真正视富贵为“浮云”,以功名为“粪土”。这是通过“克己”及“毋我”的精神修炼而来的“智慧”,也是庄子“撄宁”及孟子“四十不动心”的境界[4]。出于“仁爱”的关怀本愿,儒家对社会及理想,必然有一直下的承担。这就需要运用其“不惑之智”, 以谋求社会人生的改进。譬如孔子“正名份”、“行教化”, 即是要使人知道自己的地位角色,各各尽伦尽责, 充量发挥才情性智,严格恪守道义使命,实现由个体的“善”到社会整体的“善”的文化理想。而“礼”作为一种客观的制度形态,也存在非人性化的“异化”可能,所以孔子主张以“仁”的内心世界的情感和理性为本体依据,权衡时代内容的变化和社会生活的需要,因时制宜, 灵活损益,要在使“礼” 符合“人”的真实“本性”与“情感”,有利于“文化生命”的运作与创造。“礼”僵化陈腐抑或具有活泼的生机, 直接表现为“人文世界”纯真生命是受到窒息压抑还是如如流行,亦是民族精神气质振奋与否的标志。诸如此类的社会人生问题,都离不开“不惑之智”的广泛展开和妙用。
“不惑”之“智者”, 已熟悉“人文知识”,深知“人文价值”, 领会“文化”精义,了解人与人、人与世界的本源性关系,透悟人在“人文世界”的行为意义, 即所谓“心通于道,而无疑于天下之理”(《孟子·公孙丑》)。他只是以活泼泼的“人文态度”,通过自己的本体买践学行为,去积极落实人类共同的“价值”与“理想”, 而一切的人生实践行为,在智慧之光的照耀之下, 都是生命本体或本质的践履,都自有其“意义”和“价值”,都无不源于本心——心不容已, 无疑无惑, 无畏无惧, 自得自如,胸次悠然。这在道德上已是很高的境界,但仍只是社会人生的“觉者”, 尚需向上一层,进一步把自己的“主观格局”开尽, 才能成为宇宙世界的“大觉者”, 进入“知天命”的宗教性的境界。
四、天道与人道的贯通:五十知天命
“四十不感”尽扫一切“迷妄”与“惑疑”, 已是有限人生的重要突破;“五十知命”透悟生命及天道宇宙,则更是生命提升的钜大飞跃。四十岁时已知人、知物、知自然, 现在要更上层楼, 再次拓展生命的空间, 知“命”、知“天”或“天道”。孔子说:“不知命, 无以为君子。”(《尧日》) 此即显示“知命境界”对人生的重要, 是孔门下学上达契合“天道”的必经法门。
何谓“命”或“天命”? 孟子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孟子·万章上》)“命”或“天命”即人力之外的客观力量, 或不由人本身决定的“结果”或“限度”。“生”与“死 ”本质上就是人的力量之外的属“命”或“天”的因缘大事, 不是人能主动决定、主宰、改变的,一方面需要以存在的勇气来勇猛面对, 知“命”知“天”自觉承认质碍肉体的生命有其本来的局限性,不孜孜以求长生或不死;另方面也理当置之度外,立“命”“正命”从容开辟广阔精神世界的无限性, 不回避人生应有的“责任”和“使命”。因为“生”“死”虽不由人选择亦无法选择, 怎样的态度生、怎样的态度死却是人能自作主宰。自由决定的,“知命”的态度用孟子的话说,就是“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尽心上》)。王阳明亦谓:“死生夭寿, 皆有定命,吾但一心为善, 修吾之身, 以俟天命。”(《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人所要做的只是尽其本心本性,无止息地从事他应作的“道德事业”, 将主观的努力开尽, 不埋怨“命运”的好坏, 不计较“生死”的结果,亦不将好坏与结果一切委之于宿命而听任自然。不仅不因人的“必死性”而烦恼, 反而激发起更加强烈的社会关怀和人文信仰。这是何等的悲壮, 何等的惊天地泣鬼神! 孔子“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已有了真正的落实,此即“生死智慧”上的“知天命”的超越境界的豁然朗现。
“生死智慧”也可说是“知天命”境界转出的智慧,这一智慧因与“终极存有”相关而使儒家的道德生命及其所从事的道德事业透显出无限的庄严。因为“死”作为一个与人的生命存在、精神存在密切相关的终点, 更加凸显了人生价㥀及终极意义实现的紧张性和紧迫性。而人也只有透过终极承诺以寻求终极实在, 在终极关怀和终极意义中安顿生命, 才能化解这种紧张性和紧迫性。“逝者如斯夫, 不舍昼夜”(《子罕》), 即表达了孔子对生命流逝及其短暂,人必须突破局限以求历史性的超越,而最终将个体生命的有限转化为群体生命生生不息的无浪的慨叹。人的存在尽管是有限的,自由也是有限的,然而人却要凭借勇猛的精神力量对此有限进行超克,透过生死之大限领会、体认、证悟、契入终极存在与终极意义, 从而最大限度地彰显生死实存主体的无限自由,亦即面对死亡的威胁,面对“有限性”的挑战,从而觉醒真实本然的纯净心性, 护守人类的基本价值,并一刻不容迟缓地在世俗人间从事价值与意义的创造活动, 将终极意义的落实当作生命实现每时每刻不容忽视的根本任务。人虽“有限”而可“无限”, 人虽不“自由”亦终可“自由”。“有限”与“无限”, “不自由”与“自由”并非不可跨越的对立两极, 如何立足于现实生命的内在限度, 承认现实“自由”的可能范围, 又达致“超越”、“ 自由”、“绝对”、“永恒”呢?依中国文化的价值立场,此即在于积极入世,自强不息, 在于从尽心知性的实践中获至超越,在人生责任的奋励中上达“天道”“天德”,把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全幅展露,跃入无限广袤的“精神本体”的宇宙天地。儒家不必求助彼岸, 依附神恩,借重上帝, 凭籍梵我等外在力量, 一样能透过“生死”获至神圣的超越, 并树立起崇高的人生责任感,维护有“死”的存在的生命尊严。这是既肯定现实又超越现实的沟通“人 ”“天” 及“生”“死”的智慧, 是透过生命成长、自我实现的漫长心路历程,工夫步步踏实达至的高度“精神性”、“宗教性”的殊胜境界。

“莫之为而为”与“莫之致而致”, 也表现为人力之外的其它各种“偶然性”力量。人不仅生活在“合规律”、“合目的”的必然性世界中,而且也面对一个变幻莫测、波谲云诡的“可能性”的“偶然世界”,“必然性”“合规律性”总是透过具体的、无尽的“偶然”表现出来, 于是, 人注定要穿行在“偶然性”中,去争取那躲藏在“偶然”背后的“必然”。人固然要在变幻莫测的世界中施展自己争取“必然”的才能,从而竭尽生命的―切努力;但同时也需要种种外部“客观条件”不期而然、不期而遇的“合作”或“配合”, 表现为“天公”是否“作美”,“命运”是否“亨通”。“天公”是否“作美”在人的力限之外, “命运”是否“亨通”也在人的掌控之外,就是“命”或“天命”。孔子说:“道之将行也欤? 命也;道之将废也欤? 命也。”(《宪问》)又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 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 匡人其如予何?”(《子罕》)人生就是一场任务,为一大事而来, 为一大事而去, 人只要尽“性”践“仁”, 尽了应尽的人生义务,道德责任与精慰藉就在其中了,至于外在的结果如何,一切可以不计。而尽管“天道”茫茫,“天意”难测,“天命”难知,令人无限敬畏,人一旦这样作了,即是上达了“天道”,符合了“天意”,执行了“天命”,令人无限敬畏的超越外在的“天”, 亦可是内在于人可亲切感受、切身体验的“天”。所以,自知并努力完成自己的“人生任务”或“人生使命”,即是对外在超越的“天命”有了透悟和了解, 反之亦然。“使命”与“天命”联结,“人性”与“天命”互融, 人穿行在变幻莫测、波谲云诡的“偶然性”中, 仍能浩浩然与“天地”共生、与“天地”并立,不丧失自我的主宰——听命、任命、宿命;亦不怨天尤人——躲避“命运”、回避“偶然”。一任“偶然性”的惊涛狂澜袭来, 人依然一往直前胜似闲庭信步。孔子一生为实现价值理想而四处碰壁,甚至有道穷浮海居夷之慨叹, 但 “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八佾》), 强烈的使命感仍使他敢于易天下之滔滔, 表现出以行“道义”本身为目的, 此外则无所顾虑的伟大生命自觉。在“知命”或“知天命”的境界中, 可说是无往而非“道”,无往而非“义”,无往而非“工夫”,“人道”已与“天道”贯通,“小我”也转化成了“大我”,人也就具有了超越时空的精神伟力,能够克服一切归属于“可能性”的人生困难。这是实存主体透过“偶然”的承担、认同而建立起来的存在智慧, 是敢于面对“偶然”的命运又不丧失主宰的“必然”的宗教性性超越智慧。
由此可见,真正的“知命”,由于在生命深处领悟了无限超越的价值依据, 涌现了活泼内在的创进源泉, 会主动地投人上存与生活的世界, 充满了道德和精神的自信,必然会在生活中积极面对各种人生的不幸,体验神圣庄严的超越。其所以能充满自信, 其所以能直面各种人上与社会的不幸,乃是由于生命早已跃入了终级存在的境域, 生命的意义与终极形上的“本体”已合为一体。在终极关怀的绝对性、无条件性面前, 诸如成败、得丧、荣辱、毁誉以及一切幸或不幸,都必然显得次要或可以放弃,都必须以听命的姿态心甘情愿地服从于前者。

终极关怀的绝对性、无条件性在道德领域, 即表现为道德要求的绝对性、无条件性, 领悟了这绝对性、无条件性的人生“使命”,即是严格意义上的“知命”。终极关怀的绝对性、无条件性在超越领域, 则表现为“天命”“天意”的绝对性、无条件性,体悟了这绝对性、无条件性的“天命”或“天意”,亦同样是严格意义上的“知命”。而“道德”的领域与“超越”的领域乃是同一个领域,“人性”与“天道”在究极根源处原本同一, 在道德实践中即能超越, 在尽心知性中即可体现“天道”, 人在既内在又超越的终极意义中, 感到了能“与天地参”的伟大创造源泉。因而人虽认同和承担起“偶然”与“有限”的艰难命运, 仍可生出“必然”和“无限”的人生自信。实存主体的现实存在和形上化的本体存在不仅不疏离或分裂, 反而更加融洽统一为精神生命安顿和超越的理想化存在处所。
在这一意义上,“知命”的境界即是“本体”(存在)如实呈现的境界,“本体”( 存在 )如实呈现的境界亦即“现实生命”与“宇宙生命” 统一的整体境界。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 百物生焉, 天何言哉”(《阳货》);又说“知我者其天乎”(《宪问》),“天生德于予”(《述而》);都是这一境界的自然流露。“惟天之命, 于穆不已”,此天之为“天”,“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此人之为“人”——“心灵”与“天意”契接,“人性”与“天道”贯通,“凡俗”与“神圣”不二, 本体善与伦理善合一, 人在大化流行的茫茫“宇宙”中不仅不孤独, 反而时时处处感到“终极意义”的呈现;“知命”或“知天命”者已不仅是社会人生的“小觉者”, 而且更是天地宇宙的“大觉者”。“宇宙内事即己份内事,己份内事即宇宙内事”(陆九渊语 ),“知天命”不仅是人生社会的豪迈承担者, 而且也是天地宇宙的气魄承担者;不仅是社会中的人,同时史是宇宙中的人——遨游于“宇宙”大化之中, 与“天地”精神来往的人。
五、境界自由与生命圆融:六十耳顺与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
“六十耳顺”已是精神自由的“本体”境界, 亦即人性实现的“圣境”的呈现。在此“本体”境界中,人已超越了自己的有限性,彻悟了人生社会与宇宙世界的真实,在诗意与和谐的境界中徜徉。孔子以“耳顺”作象征概括言之, 颇能点染这一境界的精神实质。“顺”字既说明主体内部的自由境界的“诗意”与“和谐”, 也点出了外部宇宙静谧化的“生命韵响”的“悦耳”。而“耳”字更有“精神性”意味——对主体“心灵”世界与客体“宇宙”世界的“精神性”聆听, 凸显了“天”“人”贯通,“天”“人”合德,“物”“我”浑然同为一体, 诗意般澄明朗现的意蕴, 展示了“圣域”境界中的“理智之直观”或“直观之理智”的明觉观照。因为“圣域境界”中的“聖”字, 其上即着一大“耳”,“耳”后紧从“口”, 正好暗示了对“心灵”世界与“宇宙”世界的精神性“谛听”, 以及“谛听”后发自本心明觉的“言说”;下着一“王”字, 三画而连其中, 亦指明了对“天”“地”“人”的参通。与精神性的“谛听”相连的, 乃是本源性的、基始性的“本体”世界, 亦即与终极实在密切相关的“整体世界”, 而非思维慨念或逻辑范畴中被知性肢解了的残缺的“世界”。西方文化传统长期把“世界”视为“思”的对象,“世界”并不直接“呈现”于人的面前, 必须经过“理性”的环节加以把握。有趣的是这一方向在当代也有了转变的趋势, 胡塞尔的“真在”( 真理 ) 就不是“想”( 纯理智的思 ) 出来的, 而是“看”(“理智”与“直观” 结合的看 )出来的,。而海德格尔的“真在”( 真理 )不仅不是“想”出来的、“看”出来的,更是“听”(“理智”与“直观”结合的听)出来的——语言是存在的家, 在言语的“听”与“说”的敞亮中呈现世界, 而且“听”在“说”先, 本身就是“语言”的本源性的意义。[5] 海德格尔的“听”, 极类似孔子的“闻道”, 是心灵宁静明觉状态下, 对人文世界及宇宙天地的“意义”的领悟。冯友兰先生以“而已”训“耳”,以为“耳”即“而已”之急言,讥评以“耳为耳目之耳”,乃“望文生义”。[6] 于是, 此“境界”之活泼“意趣”全部索然,盖即未体会“耳”字之妙义无量欤?
精神高度“自由”的“本体”境界,当然也是与万物“通”而不“隔”的实存主体境界。《说文》:“圣,通也, 从耳。”《尚书·大禹谟》:“乃圣乃神, 乃武乃文。”孔传:“圣, 无所不通。”前已云“聖”字从“耳”, 内涵“谛听”初谊, 由此引申为参通“天”“地”“人” 之“通”, 再引申即为德行高尚的“圣贤”。“耳顺”之本体境界,此三意均可蕴含其中。心灵的“聆听”即是生命向“天地”及“宇宙”的敞开和相通, 使自己的“生命”与宇宙万物的“生命”浑然一体,即内即外, 无内无外, 内外打通, 天人合一。张载说:“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正蒙·大心篇》) 程颢亦说:“圣人之心, ……合内外,体万物。”(《遗书》卷三) 即指此“生命”与“生命”息息相通的即“本体”即“整体”的境界。而此“通”的“本体”或“整体”的境界, 即是“仁”或“圣”的“实然”本真境界。因此,程颢又说:“仁者,浑然与物同体。”(《遗书》卷二 )王阳明亦说:“心学纯明而有以全万物一体之仁, 故其精神流贯,志气通达, 而无有乎人己之分, 物我之间。”(《传习录》中) 生命质素提高的过程, 即是内心深处“仁”的无限“感通能力”不断自证自知并“通”出去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高度精神性的“自由”境界也就由心性本体的“本然”, 透过时时处处人性修持及自我实现的“应然”, 最终转化为实存主体当下的生命“实然”,代表了主体人格的伟岸挺立与自由意志的全然开显。
实存主体契入、彻入“耳顺”境界,既来源于生命质素的不断提高, 也来源于对一切是非得失的超越性摆脱。“耳顺”即意味着经过长期的精神修炼, 在“不惑之智”的基础上,进一步由“道德境界”直入“天地境界”,不仅摆脱了一切烦恼、怨恨、沮丧、压抑、焦虑等患得患失的情绪,而且廓然大公、物来顺应, 以宇宙之“心”为“心”, 与“天地精神”同体, 如程颢所说:“天地之常, 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 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7] 此时转出的智慧之境, 有如佛家教门的“大圆镜智”。心体昭然明觉, 虚明鉴照, 无染无著, 遍润万物, 彻上彻下脱落殆尽,身心无入而不自得。然而与佛家不同的是, 儒家教门的“耳顺”智慧, 虽无心安排而出于“ 自然”, 又无一不是“道德”的高度自觉的行为。

如此再向上一跃,就由“耳顺”契入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精神妙境, 生命至此亦获得一无限“圆融”(圆满、圆善)的意义。因为“欲”作为一种发自真性本心的意向性行为,如孟子所说“可欲之谓善”(《孟子·尽心下》),必然表现为与“善”密契一体的行为上的“应然”,乃是不受任何外部条件限制的彻底的自由意志;然而不受任何外部条件的限制,又自然地符合外部社会的正义原则及与之相应伦理规范。所以,严格地讲,自由意志必需始终不离儒家所强调的本心仁体,本质上即是一种自发自律的精神行为意向。倘若借用䄶家的表述,也可说“从心所欲”已契入了“心自在”妙境,“不逾矩”则跃入了“法自在”胜境(参见蕅益智旭《四书解·论语点睛补注》。此时一举手,一投足, 都无不是无限“道心”的如如流行, 都无不自然而然地流露, 又自然而然地正确——不需规范, 亦合乎规范, 或合规范地自由,自由地合规范。其境界已上与天齐, 肉身成道, 道与身合;其生命已通体透脱, 高明博厚, 洽然谐化。此即孟子所说:“充实之谓美, 充实而有光辉谓之大。”(《孟子·尽心下》) 人在此境界中,“人心”与“道心”,“未发“与“已发”,“静”与“动”,“内”与“外”,“知”与“行”, 原本一体, 如如呈现, 人格气象壁立万仞, 真善美完全统一。既不丧失一己之个性, 浩气充盈天地及宇宙;又满腔悲心与恻隐, 与万事万物同仁而一体。“随心所欲不逾矩”表明了主体高度“精神自由”的熟化境界, 而“精神自由”熟化的极境即是生命与行为的现成性圆融与本真性完善。
生命与行为的圆融与完善, 乃是由于感性的生命完全“净化”, 人性已臻于无执熟化的境界, 心体超越究极的价值根源亦全然朗现。在此超越心体的遍润圆融鉴照下, 一切由经验自我虚掷出来的二元对立都立刻消解, 万事万物无不各有其合理的价值秩序而呈现意义, 透过无执熟化的“人性”境界看到的, 只是绝对公平无争的“存有”的世界, 如如呈现的亦为诗意的在其自己和是其自己的“物自体”存在。内在的“心性”修养已臻于完美, 外在的“生命”气象必显发为圆融。内外浑然一体, 如如圆融不二,“体”“用 ”“显”“微”只是一机, “心”“知”“意”“物”只是一件 (王龙溪语), 美哉妙哉,不可思议,不可言诠,亦无从比拟!。
然而,仍䅌需强调的是,儒家的生命超越与圆融毕竟是世间道德意义的“内圣外王”之“道”, 不会亦不可能脱离人类世间活动而求一己之生命“圆融”与“完善”。“不逾矩”( 发而中节 )即说明了由规范的必然王国到超越的自由王国, 再由超越的自由王国回到规范的必然王国, 在现实世界中落实生命的价值理想, 从而建构人人“共在”的主体间性的“自由王国”的过程。这就与道家的 “逍遥游”、佛家的“大自在”有了很大的区别,尽管“游”的精神与“自在”的诉求亦同样为儒家所重视。只是在儒家看来,“圣人”即“平常人”,“圣域境界”即生活世界的境界,而生活世界的秩序即是宇宙秩序,即是道德秩序, 关怀“此”即关怀“彼”, 关怀“彼”即关怀“此”, 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相即不二,境界超越与磨难奋励相即不二。因此,人是宇宙间各种活动的“参与者”与“创造者”,负有使宇宙及社会人生“完善”的“生命责任”。万物的存在都有其内在的价值,都是生化创进过程中的生命有情物,人应促进天地万物生态的“和谐”, 参赞天地万物演进不已的“化育”。人当然更是历史文化各种活动的“参与者”与“创造者”,完善社会人生更是本己份内义不容辞的“生命责任”。在强调自己的独立性、自主性、自由性的同时,也1尊重他人的独立性、自主性、自由性。一旦个人受到迫害,社会遭遇苦难,人类面临不幸,无论其生存窘境是物质境况的或精神现象的,都必然戚然忧然, 痛心疾首,视人之苦难为己之苦难,以他人之不幸为己之不幸,于是拳擎恳恳,奔走呼号,不遗馀力,思有以救之。孔门倡“博施济众”,孟子讲“仁民爱物”[8],便具体体现了这一“精神”。而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其所作所为,都出于一己之自由意志,非特心不容已,亦如如自然,一切都只是本心真性的流行发用,沛然莫之能御地展开。一方面依“生命”的真实体认转出对文化、历史、民族、社会的责任承担, 悲悯恻怛,忧患痛心, 急切拯救, 死而后己;另方面又由“本心”“本性”的观照而超拔于文化、历史、民族、社会之上, 顶天立地, 风姿卓荦, 乐天知命。可见生命圆融亦是忧乐圆融,凡圣圆融,生死圆融,价值意义的圆融……。经历长期生命磨练而达至的“从心所欲, 不逾矩”境界,既满含了无限超越、无限自由的终极性精神价值和哲理旨趣,也蕴藏含着充满了日常生活内容的深切性人文关怀与人道主义情操。

《易传》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宇宙生生不息, 其基本的原则即是“致中和, 万物育”(《中庸》)。“知命”之时的人生境界,对此当已有深切透悟。而境界自由、生命圆融的人生,更对宇宙生命的奥秘洞悉无遗。人与宇宙息息相通, 宇宙的精神即是创进或创造, 人沐浴在盎然充沛的生命流行化境之中中, 亦同样要富于创意或创造,如此才能不负人生,德配“天地”。生命本质上即是创进不已,充满生机的, 如宋儒所说:“仁本生意, 乃恻隐之心也。苟伤着这生意, 则恻隐之心便发。”(《朱子语类》卷六十八《易四》) 因而一旦达致“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 就必然会重视生命的价值, 赞扬生命的意义, 在宇宙创化的参与活动中感受自然生命与人类生命的交融互摄,体悟无穷无尽的生机与妙趣,同时又将此自由创造的生命转化为人文世界的精神态度和生活风范, 努力激发文化传统生气勃勃的创造伟力,由一己的主体的“自由”去谋求更大范围人类群体“不逾矩”的“自由”, 无论个体或群体,着眼于人人都在其中的永恒福祉,都务必使生命更趋圆融,社会更臻完善。这既是儒家长期高悬的人文理想或道德理想, 更是孔门对无内外之分的“生命”本质的存在彻悟与实践。
六、孔子生命成长观的现代性启示
生命成长的过程, 不能脱离社会生活必需的实践,不能不经历复杂人生必须经历的一切, 其中有磨难, 有奋励, 也有提升, 有喜悦, 最终在此完整的人生过程中实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进入与终极存在、终极意义合一的崇高胜境。生死界限的超越, 实存主体的挺立, 精神境界的自由, 生命意义的圆融, 诸事在此境界中亦一时并了。在现实的实践中即有阶段性的境界跃升, 即能突破生命局限以安身立命。这是一种东方文化特有的生命智慧或人文智慧,也可说是―种即道德即宗教的生命智慧, 一种以动态、实践、提升、超越的生命成长观来规定“人”、解释“人”的活泼智慧。长期以来, 西方文化传统一直倾向于把活生生、活泼泼的“人”界定为思辨系统的静态逻辑概念或演绎推论范畴,“人”只是形式的观念的剥离于具体生活世界的有本质无内容的抽象“存在”。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中国文化生命智慧,可说至今仍不失其具有普遍意义的殊胜和精彩。
当今世界的人类, 除面临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资源枯竭、财富浪费等外部危机外,还面临着深刻的人性异化、精神下陷, 意义丧失, 生命迷茫的内部危机, 科学累积的成果愈多, 人心愈向外贪婪奔驰;工具理性和技术统治愈强大压抑, 生命意义及精神自由的空间愈狭小。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 物质巨大丰富的同时,感到的却是人性的扭曲,自我的“物化”。如何从高瞻远瞩的角度使人一念觉悟, 从根本上关怀人的生命本质及具体成长呢? 重新回到富有生机的文化传统,走向人类精神生命的深层, 挖掘有关净化“人性”的人文资源, 建构有利于每一个体生命全面成长的现代文化, 在合乎“人性”合乎“人道”的前提下, 创造二十一世纪的历史, 从而响应现代人类面临的问题, 应刻说中国文化在这方面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孔子的真思想、真精神在这方面也是可以再建构和再发展的。

孔门生命成长所要经历的人文修养阶段和精神发展境界,自律与他律乃是一个长期复杂互动的过程,。尽管相对而言他律仅为第二义之事, 但消极的制度架构仍是生命成长及境界自由的重要前提保障。“积极自由”的提倡并非就意味着否定“消极自由”,二者必须形成一个互补性的张力平衡结构。生命成长在“内圣”开出新境界的同时, 也有必要由“内圣”开出新外王。譬如如何依据“仁”重建新时代的“礼”,而“礼”作一种社会规范或文明体系,如何体现“一体之仁”,如何实现社会正义,从而不断扩大儒家“居仁由义”文化理想事业的范围天地,就是“生命成长”的学问迫切需要解决的大问题。限于主题及篇幅, 当另撰专文讨论。
孔子的思想, 渊懿浩博;孔子的精神, 和平雍穆。伟哉美哉, 其在斯乎? 本文虽试作对话性诠释, 然仍仅为原书之“眉批”或“夹注”, 是边缘性的非“正文”的“文本”。至于疏漏不妥之处, 则有待高明指教匡正。
注释:
[1] 《论语·为政》,《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2461页。以下凡引《论语》,均仅出篇名,并夹注于正文中,不再另标明具体页码。
[2] “志”与“意”本来可以互训,如许慎所说:“志,意也;意,志也。”可说既是理性意志,也是情感意志,体现了内在生命的终极心理行为,不妨释为与价值理念相关的自由意志,亦与康德的实践理性相通。许说见《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17页。
[3] 熊十力:《十力语要初续》, 台北乐天出版社1971 年重排本, 第 186 页
[4] “撄宁”说出自《庄子·大宗师》,“四十不动心”见《孟子·公孙丑》。
[5] 参阅叶秀山:《无尽的学与思》, 云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6月版, 第8-9页。
[6] 冯友兰:《觉解人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4月版, 第114-115页
[7] 程颢:《明道文集》卷三,《答横渠先张子厚书》,《二程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60页。
[8]《论话·雍也》:“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孟子·尽心上》:“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作者简介

张新民,字止善,号迂叟,贵州贵阳人,祖籍安徽滁州,先世武进。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教授兼荣誉院长、孔学堂学术委员会委员、贵州阳明文化研究院副院长、贵州省文史馆馆员。兼任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华孔子学会理事、中国明史学会王阳明研究会副会长、中华儒学会副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贵州省儒学研究会会长等。长期从事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研究,治学范围广涉文、史、哲等多方面领域。

来源:“亲民之道”微信公众号 2023-09-28
编发:中国文化书院(阳明文化研究院)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 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