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作者简介
戴岳,博士,贵阳学院阳明学与黔学研究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传统文化、伦理学;刘海涛,博士,贵州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易学文献、明清文学。
02文章摘要
对于贵州建省后首位被“海内群以名臣大儒推之”的黔中学者孙应鳌的学术渊源,自清末黎庶昌以来,学术界基本形成了一个共识,即认为孙应鳌是在十九岁时见到泰州王门的徐樾才开始接触心学的。然而,重新梳理历史文献却发现,孙应鳌因少年读书时没有明确的师承,所以“不立门户”而博览众家,其入手处在陈献章、王阳明的心学思想,而对蒋信的学说也有所了解。因为“学遂通”,故徐樾“一见而大奇之”。入仕后,孙应鳌又在蒋信的影响下,转向“得定性求仁之学于宋大儒程纯公”。中年后“归本于学孔”,最终形成了“以求仁为宗,以尽人合天为求仁之始终,而其致功扼要在诚意慎独”的思想。孙应鳌是黔中王门的代表人物,其一生学术历程受蒋信的影响颇深,而蒋信在黔期间的讲学活动是继王阳明之后的最大规模的一次学术输入,不仅直接培养了马廷锡、李渭、孙应鳌等黔中王门第二代弟子,更是涵养了黔中王门重视躬行实践的品性,可以说是黔中王门学术思想建构的直接指导者,在黔中王门中占据着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深入考证这一问题,对于重新思考阳明悟道前贵州的学术、黔中王门学术思想的建立以及历史地位,均有着重要的意义。
孙应鳌(1527—1586)是晚明黔中王门心学大师,贵州建省以后首位被“海内群以名臣大儒推之”的思想家和教育先驱。孙应鳌的学术活动,不仅使中断了千余年的贵州学脉得以恢复,而且推动了黔中王门学术思想体系的建构,将贵州阳明心学推向了一个令人瞩目的高度,“一时名德巨公争相引重,黔遂居然邹鲁矣”(贺长龄《清平县志序》)。作为晚明黔中王门的集大成者,关于孙应鳌与阳明学脉的渊源,自晚清著名外交家黎庶昌在出使日本期间发现国内早已失传的《督学文集》以来,学术界基本形成了一个共识,即认为孙应鳌是在十九岁遇到来贵州任提学副使的泰州王门的徐樾,继而受业,才始得王阳明、王艮之学。然而,重新梳理历史文献,笔者却发现孙应鳌因少年读书时没有明确的师承,故能“不立门户”而博览众家,但其入手时已经接触陈献章、王阳明、蒋信的心学思想。孙应鳌十九岁时以儒士应乡试,正因为“学遂通”,督学徐樾才“一见而大奇之”。因此,有关孙应鳌学术思想的师承,尤其是学术历程尚有许多问题值得商榷,这对于全面深入了解阳明心学的发展以及黔中王门学术体系的建构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万历六年戊寅(1578年),孙应鳌的《学孔精舍汇稿》刊印。该书是一部具有全集性质的著作,时任云南提学的刘伯燮(1532—1584)在为其作序时有如下的表述:“先生自少颖悟绝伦,博极群书,时已志于道;长游四方,得定性求仁之学于宋大儒程纯公;中归本于学孔,故是稿标以‘学孔’云。”刘伯燮解释了《学孔精舍汇稿》一书以“学孔”命名的原因,但也可看作是对孙应鳌一生学术历程的总结,即少年时的志于道、入仕后的得定性求仁之学、中年归本于孔子。学术界虽也有学者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但没有展开具体的论述。本文期在前贤的基础上,对此问题作一细致的考论。
一、少年时的志于道
刘伯燮说孙应鳌少年时“已志于道”,即志于求心学之道,如孙应鳌在《梦阳明先生述怀》中说的“平居学道心”之道,而其研习的路径则是从寻孔颜真乐处入手,对此孙应鳌的弟子温纯曾有明确的记载:“初,先生自弱冠学道,以默识寻孔颜真乐。”“默识”出于《论语·述而》中“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其本义是把所见所闻的知识默记在心里而不言,皇侃、邢昺、朱熹等人对此的注释皆是此意。然而,宋明诸儒从孟子的“反身”“思诚”出发,则认为默识“是消除了主客、能所、内外、物我界限的顿超直悟,是浑然与天道合一的大彻大悟”,即超越知解情识的限制而对本心的体悟,程颢、杨时、罗从彥、李侗以及湛若水、王阳明等人对此均有不同的解释。“寻孔颜真乐”是从宋儒“寻孔颜之乐”衍生出的命题。“孔颜之乐”是指《论语·述而》中孔子所言己之乐“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以及《论语·雍也》中孔子称赞颜回之乐“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对于“孔颜之乐”,从孔安国、何晏、皇侃以至邢昺、鲜于侁等人皆认为在于“乐道”。宋明理学的开创者周敦颐则不赞同“乐道”之说,而认为“孔颜之乐”是“一种超越物质功利计较的精神之乐”,并让程颢、程颐“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程颢、程颐也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只能从侧面给予解释:“使颜子而乐道,不为颜子矣”,“箪瓢陋巷非可乐,盖自有其乐耳。‘其’字当玩味,自有深意”。朱熹则十分推崇程颢的观点,认为“元自有个乐”,因此也强调“不要去孔颜身上问,只去自家身上讨”。与宋儒探究“孔颜之乐”不同的是,明儒则讨论的是寻“孔颜真乐”,如:陈献章曰“自然之乐,乃真乐也”(《与湛民泽》),王阳明也曾说“讲习有真乐,谈笑无俗流”(《诸生夜坐》)、“每日闲坐时,众方嚣然,我独渊默。中心融融,自有真乐,盖出乎尘垢之外而与造物者游”(《示徐曰仁应试》)。“真乐”也是阳明后学常谈论的一个话题,如:王艮云“须见得自家一个真乐,直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然后能宰万物而主经纶”(《王心斋全集·语录》),王畿云“乐至于忘,始为真乐”(《答南明汪子问》),等等。
温纯虽然说孙应鳌“以默识寻孔颜真乐”,但并没有具体的说明,同时也没有其他相关的文献记录,所以我们无法了解孙应鳌是如何“以默识寻孔颜真乐”的。然而,可以确认的是,孙应鳌之所以选择这个论题,应该与当时贵州阳明心学的发展有关。自从“龙场悟道”后,王阳明即在龙冈、文明书院讲授“知行合一”之旨,诸生环而听者以数百计,“自是贵人士始知有心性之学”。与此同时,王阳明“用是风厉学者”,土人感其德,翕然向风,黔俗亦为之大变。王阳明的讲学促成了黔中王学发展的第一个高潮,但随着王阳明离开贵州,特别是嘉靖八年己丑(1529年)朝廷下旨停王阳明世爵恤典并禁其学术,王阳明所开创的讲学活动在贵州也渐趋消沉。嘉靖十三年甲午(1534年),王阳明的私淑弟子王杏巡按贵州时,“深感夫子教化深入人心”,但文明书院已经荒废,黔中王门弟子汤冔、陈文学等人遂多次恳请立阳明祠“以慰士民之怀”,王杏乃建阳明书院,并告诫诸生要“言先生之言”“行先生之行”“思先生之思”(嘉靖《贵州通志》卷六王杏《新建阳明书院记》)。时任贵州按察使的王门弟子胡尧时则“刊守仁所著书于贵州,令学徒知所景仰”。黔中人士对王阳明的著作也是“家诵而人习之,若以得见为晚,其闻而慕、慕而请观者踵继焉”。与此同时,王杏积极倡导“求在自身”的为学精神,其在《书文录续编后》中曾言道:“先生以道设教,而贵人惟教之由无他也,致其心之知焉而已矣。知,吾知也,其心之自有者也。先生诏之,而贵人听之,吾有而吾自教焉尔。”这里“知,吾知也”即是强调自我的体认、感知,所以说是“吾有而吾自教焉尔”。所以黔中士人读阳明遗作而求其道,并不是在王阳明身上求,也不是在其文字上求,而是在求道者自身上求:“故昔日之所面授,此心也,此道也,今日之所以垂录,此心也,此道也,能不汲汲于求乎是?求之者,非以先生也,非以其文也,求在自身也。”“求在自身”的为学精神对黔中士人产生了重要影响,使得黔中士人能博采众说而少门户之见,注重自我的体悟而不人云亦云。王杏等人的努力为黔中王门学术的兴起做了充足的准备,而真正将其推向高潮的则是楚中王门弟子蒋信。
嘉靖十八年己亥(1539年),蒋信来黔任提学副使。蒋信是王阳明的早年弟子,后又师事湛若水,所以“不仅承续了阳明一派的嫡传心法,亦深得白沙—甘泉一系的血脉神髓,可说是姚江之学与江门之学的共同承祧者”。这是从“阳明中心论”出发所得出的结论,而“若不以王阳明、湛若水为绝对视点,将镜头聚焦于蒋信个人思想脉络的发展历程,即可发现他并非王、湛之骥尾,而是已开始突破既定思想范围的鳌头”。显然学术界已经注意到了蒋信与王阳明的不同,所以蒋信的出现也意味着学术即将迎来新的变化。而且蒋信入黔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那就是蒋信不仅把黔中王门的第二次讲学活动推向了高潮,而且明确了黔中王门学术的发展方向,并直接促成了黔中王门思想体系的建立。黔中王门的兴起,最初有赖于王阳明的教诲,但亲炙阳明教诲的黔中王门第一代弟子主要是在躬行践履阳明思想以及文学作品的创作上,而黔中王门思想体系的建立,则有赖于黔中王门第二代弟子,主要是“理学三先生”李渭、马廷锡、孙应鳌的努力,而李渭、马廷锡、孙应鳌三人均从学于蒋信,其学术思想的成熟又均离不开蒋信的指导与点拨。如李渭自小即跟随父亲从学于蒋信门下,在其遭遇学术困境时,蒋信则以“求仁”之说破其冥顽,对此万历《广东通志》卷十三《名宦》中有记载:“李渭,字湜之,贵州思南籍,咸宁人。生而颖异,少从父游蒋道林之门,即志于道。……自后又作一介不取不予工夫以求入门,真是‘一介不敢妄取,一言不敢妄语,一事不敢妄为’,以印证于蒋道林,道林曰:‘此亦是硁硁然小人。’渭因翻然悔悟,自后渐觉开扩,乃知圣学以求仁为要。”这段文字中所说的“印证于蒋道林”之事,即是发生在蒋信任贵州提学副使时,这也是学术界常提及的“破楼上楼下光景”,郭子章《黔记》中有详细记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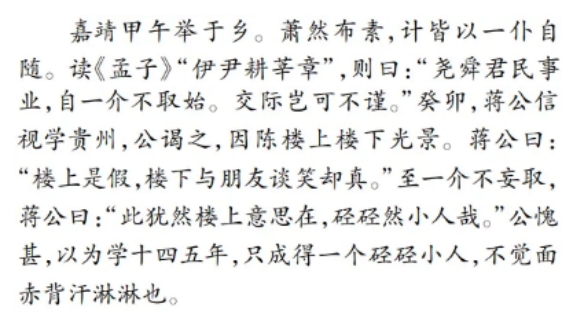
面对蒋信的回答,李渭“面赤背汗淋淋”,亦可见对李渭触动之深,这也促使李渭重新调整自己的学术方向,终成“南国躬行君子,中朝理学名臣”。
蒋信提学贵州时,重整旧祀王阳明的文明、正学两书院,“择士秀者养之于中,示以趋向,使不汩没于流俗,教以‘默坐澄心,体认天理’,一时学者翕然宗之,而心庵为之冠”。这里的心庵即是马廷锡,是蒋信的入室弟子。阳明心学本是为了挽救程朱之弊而兴起,但到了晚期,其流弊也日益明显,蒋信则“践履笃实,不事虚谈”,所以莫友芝称赞道:“楚中传姚江学者,虽有耿定向天台一派,流至泰州王艮,然后多破坏,不如武陵蒋、冀得其真醇”。也正是蒋信的“示以趋向,使不汩没于流俗”,才使得黔中王门在学术思想体系的建构时避免了流弊的侵蚀。蒋信后被弹劾擅离职守,削籍后“奉恩例冠带闲住,筑精舍于桃花冈,聚徒讲学”,此时已“谒选蜀令”的马廷锡“念所学不尽澈”,遂“投籍走桃冈,就道林居,数年卒业,乃归”。马廷锡在桃岗之时,蒋信即以“万物一体”之义教之:“心庵时有问,则举《鲁论》一二处与之点破,使之即自心之性情观焉。尧舜孔孟万物一体,宗旨可识也。”在马廷锡请归之时,蒋信又告之万物一体之义不当于静中光景求之,“昔尹和靖既悟仁体,言于伊川曰:‘静中观万事,皆平等无碍。’伊川曰:‘须是动上有此气象始得。夫一动一静之间,此天地圣神同一至妙,至妙之机要必勿失于动,然后为存存实地,聪明睿智,达天德几矣。’是故知终终之,斯可以存义”。此教诲与点破李渭楼上楼下光景是一致的。
孙应鳌也就是在这种浓厚的阳明心学的氛围中出生、成长并开始了他的学术历程。孙应鳌生于嘉靖六年丁亥(1527年),幼随其父孙衣、叔父孙袞学习儒家经典,十岁时受业私塾周慎轩门下,“学书运笔,横经受旨”。少年时期的孙应鳌即已经显示出异于常人的秉赋,“九岁能属文,授之书,辄取大义。书竟,辄瞑目危坐,不从群儿嬉,已尽发家藏书读之”,由此而“学遂通,弱冠举省试第一”。孙应鳌少年时已志于心学,最早师从何人?现有的文献资料没有明确的记录,丘禾实在《孙文恭先生传》中则说:“先生之学,初若无所师承,不立门户,至其入手,则似于江门、余姚得力独深。”这里“无所师承,不立门户”即是说明没有明确地拜师于某位名臣大儒门下,“似于江门、余姚得力独深”则是说明孙应鳌初学之时以陈献章、王阳明之学用力最深。既然如此,孙应鳌对诸多王门后学的理论也应有所了解,因为王杏、胡尧时、蒋信等人入黔为官,势必把各种思想带入贵州,而对孙应鳌影响最大的则是蒋信。蒋信在贵州时,孙应鳌正随其父孙衣在云南保山,未能结识蒋信,但孙应鳌在《祭蒋道林先生文》中曾说:“某自髫龄,慕公道德,未及门墙,有怀立雪。”显然是欲拜蒋信为师。孙应鳌少年“以默识寻孔颜真乐”可能也与蒋信有关。蒋信非常重视“默识”,认为阳明心学的核心要义即在于默识:“阳明子之学贵心悟也,心悟者,默识也。”对于王艮的“默识”,蒋信也大为推崇:“‘默识’二字,王心斋看得好,云:‘默识个甚么?识得天地万物一体。’此心斋善体认也。”其在论说自己与其他王门弟子的区别时也言道“彼以臆说,吾以默识”。“默识”也是黔中王门第二代弟子们常讨论的话题,这也可能是受蒋信“默坐澄心,体认天理”的影响,如马廷锡曾言“万卷精通乃是聪明枝叶,一尘不染可窥心性本根”,进而希望“坐破蒲团几个”以“却听反观”。许孚远与李渭也曾就“默识”有过讨论:“程子曰:‘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识者,默而识之也。识得便须存得,方为己有。时时默识,时时存养,真令血气之私消铄殆尽,而此理盎然而流行,乃是‘反身而诚’,与‘鸢飞鱼跃’同意。”孙应鳌稍晚于马廷锡、李渭,其亦从“默识”入手寻“孔颜真乐”,应该与此相关。
嘉靖二十二年癸卯(1543年),蒋信以病求致仕后便回到武陵。次年,孙应鳌才由云南保山返回清平家居,是年泰州王门弟子徐樾来黔任贵州提学副使。嘉靖二十四年乙巳(1545年),十九岁的孙应鳌以儒士应乡试时,其才华让徐樾大为震惊,“督学徐公樾一见大奇之,许必解额”,后孙应鳌果以《礼经》举乡试第一。学术界目前有一个较为共识的观点,即认为孙应鳌是在十九岁时见到徐樾才开始接触心学的,徐樾因此可以称得上是孙应鳌心学思想的启蒙者。这种观点最早出自清末巨儒黎庶昌,其在《刻孙淮海先生〈督学文集〉序》中言道:“先生当明中世,传阳明王氏之学于贵溪徐樾波石,即能洞彻良知之弊。”这似乎已经有了孙应鳌的心学来自徐樾的意思。黔中宿儒李独清在《孙文恭公年谱》初稿中则直言孙应鳌“少学于樾,渊源有自”,更是明确指出孙应鳌的心学思想来自徐樾。刘宗碧在《贵州古代第一位哲学家孙应鳌》一文中则直接指出孙应鳌是“19岁开始接受‘心学’的影响” 。至此,这种观点也被学术界广泛采纳。然而,考察相关的史料,却发现晚清以前的诸多文献,如陈尚象的《南京工部尚书孙应鳌墓志铭》、丘禾实的《孙文恭先生传》、吕克孝等的《如皋县志·孙应鳌传》、过庭训的《本朝分省人物考·孙应鳌传》、郭子章的《黔记·工部尚书孙应鳌传》、万斯同的《明史·孙应鳌传》、徐开任的《明名臣言行录·尚书孙文恭公应鳌传》等均没有提及过孙应鳌从学于徐樾。而且,徐樾是在蒋信之后才任贵州提学副使,徐樾到贵州之时,孙应鳌已经十八岁,孙应鳌说“自髫龄,慕公(蒋信)道德”,显然是很早就听闻过蒋信了,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很早就对心学有所了解,这自然是在认识徐樾之前,所以徐樾绝不可能是孙应鳌心学的启蒙之人。虽然我们无法确认孙应鳌最早是跟从何人学习心学,但可以确认的是,孙应鳌是在贵州第二次讲学活动的高潮中接受了心学的启蒙,而主导这次讲学活动的重要人物即是蒋信。
二、入仕后得定性求仁之学
孙应鳌中举人后,又经过六年的苦读,于嘉靖三十二年癸丑(1553年)中进士,由此步入仕途,这也为孙应鳌与诸多王门弟子,如蒋信、胡直、王宗沐、罗洪先、罗汝芳、赵贞吉、耿定向、耿定理等的交往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条件。入仕之年,孙应鳌即去拜访蒋信,以印证其所学。而在与蒋信的交往中,又听闻了蒋信的“求仁”之说。正是受蒋信的影响,孙应鳌则以程颢为宗,得其定性、求仁之学。
(一)与蒋信的交往
嘉靖三十二年癸丑(1553年),孙应鳌中进士。是年,孙应鳌即借经武陵之便,前去拜访蒋信,“见则未尝不造膝移日。虽旋别去,凡谭说之入耳,鼎鼎于心,又未尝忘也”。嘉靖三十六年丁巳(1557年),孙应鳌出补江西按察佥事,又一次借归省之便,“溯流桃源”,再次拜见了蒋信,“获聆謦欬”。嘉靖三十八年己未(1559年)冬十月,孙应鳌回乡省觐路过武陵第三次拜见了蒋信,“侍论道林先生桃岗三日”,并期待三月后莅官返回时再侍蒋信。岂料返回时,蒋信已于十日前去世。蒋信临终前,叮嘱其子请孙应鳌为其作墓志铭,由此亦可见蒋信对孙应鳌道德、文章的肯定。与蒋信的相见也使孙应鳌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学术追求,其曾言道:“鳌少亦知学道,见公而其志始坚。”
孙应鳌与蒋信的交往虽然只有6年的时间,而且相见的次数也仅有3次,但两人的交往则对孙应鳌的学术思想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孙应鳌与蒋信交往,一方面是印证入仕之前所学,如丘禾实在《孙文恭先生传》中即说:“入仕之日,访蒋道林于桃岗,与语三日欲证所知,而道林转以为畏友,于是先生之名益闻。”孙应鳌督学关中的弟子温纯在《归来漫兴序》中也说:“又往来武陵,与道林蒋先生相印证。”另一方面则是听闻蒋信的“求仁”之学,如孙应鳌的好友胡直在《刻〈孙山甫督学文集序〉》中即说“孙子生神颖,长学于道林子”,“学于道林子”即是学蒋信的“求仁”之说,对此孙应鳌在《正学心法序》中也有明确的说明:“从道林蒋子游,讲‘求仁’之旨”。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要义,蒋信的学术正是从“求仁”之学入手。早在嘉靖四年(1525年)蒋信在南雍太学时,南京国子监祭酒湛若水曾以程颢《识仁篇》“学者须先识仁”试论诸生,蒋信则认为孔子之所以教人者,“一则曰仁,二则曰仁”,当时学者之所以学于孔子者,“一则曰求仁,二则曰求仁”,因此孔门之学一言以蔽之即是“仁”:“立而立人,达而达人者,语其体也;克己复礼,主敬行恕,参前而倚衡者,语其方也;博学、审问、明辨、笃行者,语其功也;一贯者,语其约也;天下归仁者,语其大也。”所以蒋信强调“学为孔氏,而不于孔氏之仁求焉,吾敢信其能为孔乎哉”。从心学的立场出发,蒋信认为孔子所说的“仁”即是“吾心之本体”,是“体用一、内外一”的,因此当于“吾心之仁”求之。孔门之教本“至易至简”,但“学至于后世,其多门也,甚矣”,千载之后,唯有程颢能得其传,“孰谓千载之后,而赖有明道者乎?吾尝诵其言,而有感焉。其有感焉者,窃以谓圣人易简之传,赖有明道者发之,奈之何复寻复晦之也”。故蒋信极为推崇程颢,而对于朱熹之说多加批驳:“自紫阳开穷理之门,传之者遂失其宗,孔门求仁之学,乃为之晦而不光。”
程颢讲“学者须先识仁”,何为“仁”?在程颢看来,万物本来是一个整体,它们之间有着休戚相关的内部联系。而学道学者不仅要认识到这一点,还应该真实感觉到自己与物同体,达到这种境界即是达到了“仁”的境界,达到这种境界的人叫作“仁者”,所以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万物一体”的思想在先秦时期即已出现,直到宋代才真正上升为哲学理论,张载、程颢等人对此均有阐发。而“万物一体”的思想也被湛若水、王阳阳明等人所秉承,甚至成为王阳明思想的基本精神。受程颢等人的影响,蒋信则认同“天地万物一体为圣学根基”,为学之人必须识得这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即要识得“仁体”,这个“仁体”即是“真心”,是“天地万物公共底主宰”。而对于如何“识仁体”,蒋信认为《大学》“知止”即是“识仁体”:“知止者,功夫到极停当处,忘助皆绝,神鉴洞如,覻此物事了了,而廓然广大之体,倏然以复,有若目睹之也。即孔子所谓‘默识’、明道所谓‘识仁体’、濂溪之‘欲寻见孔颜乐处’也。”针对当时心学的流弊,蔣信又提出“默识以察其几,慎独以操其要,诚敬以存其功”,遂形成“其本为要于知止,知止为严于慎独,慎独为妙于默识,默识为融于勿忘勿助之间,其综之为成此仁于一身”的学术思想。孙应鳌与蒋信在桃岗相见,听闻的即是这种学说,这也对孙应鳌的学术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万历《贵州通志》卷十三对此记载道:“初闻蒋信倡明理学,晤论于桃岗三日,默悟审几慎独合一求仁之旨。”颜鲸在《赠淮海先生拜大中丞节制三藩序》中也言道:“已乃从道林蒋先生讲学桃岗,闻慎独、体仁之旨,大有感悟,刊落声华,潜修力造,凝神夙夜,庶几求所谓默识而心得之者,尤其实际云。”显然,孙应鳌已从少年时以“默识”寻“孔颜真乐”转向了以“默识”寻“仁体”。
虽然蒋信认为求仁体“求诸吾心,而自得焉可也”,但同时认为《语》《孟》等儒家经典皆“识仁体”之理,尤其是在见到阳明先生后,对“俗学章句之陋”更加不满,遂用心考索于六经、《语》《孟》以及《西铭》《定性》等书本之中而终有所悟,“初读《鲁论》及关、洛诸书,颇见得‘万物一体是圣学立根处’”,“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体,《西铭》备言此理,学者惟体此志”。虽然《西铭》《定性》等宋儒的经典亦言“识仁体”之理,但又有所侧重,如“横渠之《西铭》博矣,明道之《定性》约矣,其功则孟子之‘勿忘勿助’要矣”,皆不及《语》《孟》全面,所以蒋信则认为“道不稽诸孔孟,虽贯穿百家,不足以言道”(《寄学孔书院诸会友琐言》),因此非常强调要“究乎古人学问之源”(《简陆平川佥宪》)。故蒋信一路溯源,追至《论语》,正如赵贞吉所言:“夫蒋先生学以体仁为宗,敬默为实,溯伯淳子渊而师於孔氏,商赐以下不论也。”
受蒋信的影响,孙应鳌将其思考的方向也转向了“识仁体”,而“明道之学,以识仁为主”(黄宗羲《宋元学案》),因此,孙应鳌很自然地就把程颢《定性》《识仁》作为学问的根本,“尝手释程子《定性》《识仁》篇,署曰‘学孔正脉’。自是历官操行,一以为依归”。吕克孝《孙应鳌传》亦云:“公讲明正学,以定性识仁为根宗,审几慎独为门户,庶几躬行君子云。”除了程颢的《识仁》《定性》两书外,张载的《西铭》也是孙应鳌熟读之书,邹德涵在《上孙淮海公》中即言道:“公之学,以识仁为宗,《西铭》一书,盖读之熟矣。”之所以如此,即在于《西铭》一书所阐发的“天人一体”“民胞物与”的思想与程颢的思想是相通的。
(二)弘扬蒋信之说
嘉靖三十八年己未(1559年)蒋信卒,孙应鳌在《祭蒋道林先生文》中总结了蒋信的学术思想,即主张万物一体为仁,而求仁需要默识,而默识又在于慎独,“万物一体,仁乃至善。非公知止,孰为定见?求仁有要,默识无遗。非公指示,孰得所师。默识靡他,几在慎独”。这种思想也被孙应鳌继承下来。嘉靖四十年辛酉(1561年)至嘉靖四十二年癸亥(1563年),孙应鳌任陕西提学副使,督学关中。此时的孙应鳌即“以濂洛之学自认”,日与秦中诸生讲论心学,“随所疑问,应辩如响”(任翰《题教秦绪言小引》),关中博士弟子则事孙应鳌如山斗,“乃阐明道妙,揭示默识本旨,即世世可师承矣”(温纯《归来漫兴序》)。孙应鳌在课正学书院诸弟子时,即教以蒋信的“求仁”之说,如温纯在《教秦总录序》中即言:“嘉靖中,吾师淮海先生以臬大夫督秦中学,既以经义课诸弟子正学书院中,……乃取鲁邹微言为诸弟子告,其指详录中,大要以天地万物一体为仁,而其功严于慎独,妙于默识,融于毋忘毋助之间,综之为成此仁于身,使世之学士知诚意、慎独为己知几,集义、养气、主静、定性无两轨辙,即由之从经义出,而委身县官,不知有我,安知有人,是先生教诸弟子意也。”孙应鳌曾作《谕陕西官师诸生檄》以督劝师生,在“订学”条中指出“正学正道”即是学“仁”:“夫学之道大矣!圣谕首言‘正学正道’。所谓正学,尧、舜、周、孔之学也;所谓正道,尧、舜、周、孔之道也。……故圣门名之曰‘仁。’”要达到“仁”的境界,即是要“合天地民物万古而览镜之,是为一体;合一身家国天下而属联之,是为一物”,而其用功处则在于慎独、默识:“故其功之妙于慎独者,极诸默识而不漏;其知之达于悦乐者,合诸外内而罔遗。”这即是对蒋信“求仁”之说的阐发。对于如何见其本体的论述,孙应鳌则引程颢的《定性书》加以阐发:“然犹有可指以见本体者,明道《定性》之书则尝言之:人之心有所蔽,故不能适道,大率患在自私而用智,不能内外两忘,而求以廓然应物,其于道也,不亦远乎。……故明道《定性》之书,以‘无将迎,无内外’发明‘动亦定、静亦定’之旨。而所谓喜怒哀乐未发前气象,当亦不出此而观之。故放心既收,则未发气象自见,随感而应之,体浑沦无物之实,莫非自然妙用,其求静恶动之心,执动泥静之心,至此俱知其非真矣。……鉴不以无照而不明,心不以无感而不应,此酬酢之根本,理性之枢管也。”
对于蒋信的众多著作,孙应鳌认为皆是“蒇扬圣则、发摅学轨”的力作,可使“持循者不迷谬于荆榛而可蹑履窔奧”,尤其《古大学义》《桃岗日录》《训规》《讲义》四部著作更是“尽厥旨归”,因此孙应鳌“每怀是自照览”,以检省自己的言行。督学关中期间,孙应鳌则应同门之托,将此四部著作汇编为《道林先生诸集》予以刊印,以共同好。在《道林先生诸集序》中,孙应鳌称赞蒋信“闳积邃养,洞察理脉,知物我同体为言仁标准,是以于默识、慎独之旨独观其昭旷,故著述不诡于圣人”。而对于“仁”,孙应鳌也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即理、性、命皆统于仁,而此仁又会于一心:“夫圣道之大,至矣。凡往来古今间,自两仪立位,庶物成形,至不可名象,不可纪极,语其流通为理,语其实体为性,语其秉赋为命,此生生之真精,六合之内,同一原本。于是秀灵之独会于人者语其天,聪明之良,莫不兼备乎万有,贯通乎一心。故孔门直指示人,乃命曰仁,此之谓也。”“仁”又具有生生不息之能,人具有仁则能体悟到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故心无私无蔽,而要达到这种境界,又须于“默识”“慎独”上用功,如此才能“审几”以达到“合一”之境界:“人得是生生者,为心不容以有我自外,不容以有间自蔽,故必默识,然后闻见之支离可去,而必慎独,然后默识之端绪可求。去闻见之支离,然后明通公溥之用得;知默识之端绪,然后显微合一之机神。斯心所由存,生生所由不息。仁所由得,而穷理尽性至命之学所由一贯也。”此语即是对蒋信学说的总结,又融入孙应鳌自己的见解。也就是在对“以求仁为宗”“默识”“慎独”等问题的思考中,孙应鳌的学术思想也日趋成熟,所以友人胡直曾称赞道:“孙子寤道得一,自居关中寖盛也。”
(三)与胡直的交往
孙应鳌曾言其“从道林蒋子游,讲‘求仁’之旨,己乃得数见海内大人先生,以是稍有闻圣贤绪论”,“海内大人先生”即指胡直、王宗沐、罗洪先、耿定向、邹守益父子等人。与孙应鳌交往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则是胡直。胡直先从学于王阳明的入室弟子、江右学派的代表人物欧阳德,后又入王阳明的私淑弟子罗洪先之门。胡直的学说“以一体为宗,以独知为体,以戒惧不昧为功,以恭忠敬为日履,以无欲达于灵明为至”(《明儒学案》卷二十二:《江右王门学案》),虽然与孙应鳌有所不同,但在“以一体为宗”的“求仁”之说上是相同的,对此孙应鳌也曾说:“公尝从念庵罗子以学,余亦从道林蒋子以游,二先生皆尽仁之至。……余与公先后游衡山,相约诛茅结庐,共探此学之深蕴。”胡直在与孙应鳌的书信中言道:“圣人之学,自尧舜以来,相传唯仁体,故孔门惟程伯子言之尤详,越是则二氏矣。……今得来封《教秦录》读之,其中言言与鄙心協甚。即如所驳‘博施济众及康斋第一着’之说,见丈于仁体盖初有得,而后或凌迟矣。”早在嘉靖三十六年丁巳(1557年)孙应鳌出补江西按察佥事时,即与胡直有交往,“往者余两官江西,得缔交庐山子,己又数会芷厓兰水之间”。嘉靖四十二年癸亥(1563年),孙应鳌升四川右参政,次年胡直入蜀任西蜀督学使,两人同官于蜀,更是互相砥砺、互相提携。胡直曾摘取周敦颐、程颢、王阳明三人“示人先后本末,反求诸心”之语汇编成《正学心法》一书,孙应鳌在《正学心法序》中提出“寂感体用一源”之说:“寂感,人心也。寂感之间,圣人所谓‘一贯’也。虽寂而天下之故未尝不感,虽感而本然之真未尝不寂,故寂感非二,不二则仁。”并借耿定向之语说明两人学术的互补性:“楚侗子语鳌曰:‘子今为仁,庐山子其依也。’故鳌愿与胡子以此学相终身,且效于同志。”孙应鳌非常认同耿定向的这个评价,在《衡庐诗稿后叙》中孙应鳌又言道:“楚侗耿子自南都寓书余曰:‘子今得为仁之依,舍庐山子莫可究竟者。’又寓书庐山子曰:‘淮海子入蜀,其为子贺得良朋。’以余二人合并之益,即楚侗子在数千里外犹相为慰藉,则余二人之情可知已。”嘉靖四十五年丙寅(1566年),普安州人邵元善汇编刊刻孙应鳌督学陕西时的文章为《督学集》,胡直为之作序,高度评价孙应鳌对万物一体之源的认识,并认为传播孙应鳌的思想是其义不容辞之职责:“道原至一而散见于至不一。……予不能知一,而幸友于淮海孙子。方予与孙子足未相数,言未相洽,骎骎乎合矣。己而足相数也,言相洽也,不知孙子之为予,予之为孙子也。……孙子名满天下,而莫逆莫予若,序而传之,以明孙子之学,非予则谁耶?”也正是在与以胡直为代表的阳明后学的交往中,孙应鳌的“求仁”之说日趋成熟。
三、中年归本于学孔
孙应鳌在与胡直的交往过程中,不仅对程颢的“定性”“识仁”之说有了进一步的阐释,更为重要的是受胡直等人的影响,学术有了新的转向,即“归本于学孔”。早在嘉靖三十三年甲寅(1554年),胡直即有“学孔”的思想,其在《与徐鲁源宪副书》中曾说:“夫学以孔子为至,盖某自甲寅因感‘博文约礼’始知从事。……故学孔者贵得其本,不然,俾枝枝以合,叶叶以肖,窃恐模拟装缀,而圣神之内髓均莫能强似矣。”胡直的“学孔”之说因“尚未是实有诸已”,所以也遭到一些质疑。孙应鳌则对胡直的“学孔”之说给予了支持,胡直在给孙应鳌的书信中曾说:“今弟与丈从事此学,弟数年前虽名学孔,然举孔子不能无悸意,向得丈委记,甚有激发之益。是与丈相期在孔子,相见在发愤皜皜之中。古人所谓不约而同者,不在兹与?”《答淮海书》有“喜闻吾丈复起郧台,正欲得仕楚者”的记载,此是指孙应鳌于万历元年癸酉(1573年)再抚郧阳之事。由此可知胡直所说的“向得丈委记,其有激发之益”,当是在此数年之前,孙应鳌即曾对胡直有所告诫,这也让胡直获益良多。
早在隆庆二年戊辰(1568年),孙应鳌等人简摘编辑蒋信文集续集,名曰《道林蒋先生粹言》,孙应鳌在《道林蒋先生粹言序》中已经是站在“学孔”的角度来立论,序言开篇即言道:“万世论学之的则,准诸孔子。”在孙应鳌看来,孔子论学的根本即在求仁,而仁即人心,天地万物一体为仁,所以求仁即求得本心,悟到天地万物一体,即是以“一”为根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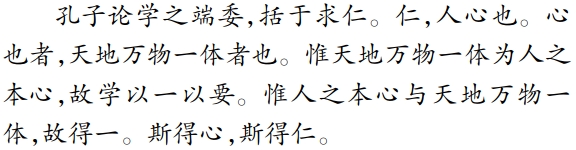
因此,后世的学者不能达到天地万物一体的悟境,则是远离了孔门的宗旨。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就在后世有内外之分,“奈何后世之学卒不能一,则孔门之旨远矣。何言乎不能一也?心也者,天地万物一体,是无内无外者也。世之是内者,遗事物以论心,其弊将游其心于空无虚寂之归;是外者,溺事物以丧心,其弊将荡其心于形器支离之末。贤知之过,愚不肖之不及,率是焉”。孔子欲救其弊,然而无内无外之间即是一,难以用语言表示,于是则列举兼内兼外的要点,如“敬直”“约礼”“义方”“博文”等,以说明内外之道合而一体亦由此可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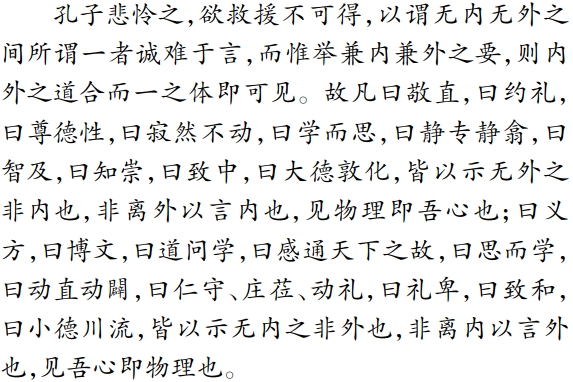
既然“敬直”“约礼”“义方”“博文”等是兼内兼外的,那么“敬义同体而并至,博约同体而并用,德性问学同体而并徹,寂感同体而并妙,思学同体而并尽,动静同体而并运,智仁同体而并到,知礼同体而并著,中和同体而并践,大小同体而并察”,这就是所谓的“几”,知己就是知此。“动矣然未形,未形矣然动,不落于有,不落于无,人所不见,为己自知”,这就是“独”。“真知此动而未形、有无之间”就是“慎独”。“无内无外之间所谓一者”,即是“默识”。借助“勿忘”“勿助”的工夫,即能达到与万物的浑然一体:“勿忘以沦于无,勿助以汩于有,允执斯中,卓尔不倚,天理流形,人欲净尽,不见天地万物之非我,不见我之非天地万物,上下四方,往古来今,浑然不己。”而《大学》所说的“知止”,也即是知“无内无外所谓一”、即是知几、即是慎独、即是默识。而蒋信的论著,“具明斯旨,学者循其言,可以入圣道,无过与不及之失,诚有功于孔门矣”。孙应鳌在督学关中时期即曾刊刻《道林先生诸集》,并为之作序。此时孙应鳌所关注的是“求仁”之道,虽然序言中说“孔门直指示人,乃命曰仁,此之谓也”,但并没有上升到以“学孔”为准的。因此两篇序言对照读,即可以发现孙应鳌思想演变的路径。
隆庆三年己巳(1569年),孙应鳌因遭言者诬陷,遂以疾请告归里,“选伟拔山之麓,得其胜者止焉,遂辟为书院,以居学徒”,此书院即为学孔书院,胡直曾应孙应鳌之邀作《学孔书院记》。之所以命名为“学孔”,即在于孙应鳌“自以平昔所学,舍孔子无由也”,这也说明此时孙应鳌已经完全转向归于孔子。万历二年甲戌(1574年),复出的孙应鳌告诫学孔书院诸友:“道不稽孔孟,虽贯穿百家,不足以言道。”万历五年丁丑(1577年)孙应鳌再次归里,以“昌明圣学,兴起斯文为己任”,筑学孔精舍于近城山麓,“日携子弟游习”。孙应鳌“归本于学孔”后,致力于《学》《庸》《论》《孟》四书的讲授。孙应鳌认为“圣门之学,主於求仁”,“圣门之学,全在求仁”,而“一部《论语》,圣人惟教人以求仁”,其在论“学而时习之”时即言道:“其第一章首提‘学’字,不言何学,则学者学此仁而已。自不睹不闻以及于起居日用,无时无处不是此学,方是时习。如此则此心之仁,无有间断,天理流行,人欲净尽,即是说。……其纲领总在‘学’字内,工夫总在‘时习’内,自得之妙总在‘说’字内。圣人所以为教,君子所以为学,不逾于此矣。”《大学》的“格物”,即是要“格得此身与天下国家共是一物”,致其知,即是要无一毫疑惑障蔽,这便是识仁体,“由此着实下诚意功夫,以正其心,以修其身,便是以诚敬存之,只此就是大人之学”。《中庸》所言中庸之道,不过尽人合天而已。而其下手工夫则在慎独,“知几者,慎独也,为己者,实落做慎独工夫也。知慎独者,可与言中庸矣”。也就是在对《四书》的重新阐释中,孙应鳌最终建构了“以求仁为宗,以尽人合天为求仁之始终,而其致功扼要在诚意、慎独”的思想体系。
四、结语
孙应鳌是黔中王门的代表人物,其学术思想的孕育、萌芽、发展乃至成熟的过程是黔中王门学术发展的一个缩影,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阳明心学发展的最新动向。孙应鳌的学术思想与蒋信有着甚深的渊源,其心学思想萌芽于贵州阳明心学讲学的第二个高峰时期,而蒋信正是这个高峰期的主要缔造者。入仕后的孙应鳌在拜见蒋信后,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学术追求,并在听闻蒋信的“求仁”之论后转向程颢的求仁、定性之说,而在整理、刊刻蒋信的著作以及讲学活动中,孙应鳌的学术思想也逐渐成熟。孙应鳌在中年后“归本于学孔”,即是在蒋信“求仁”之说基础上的丰富与升华。
蒋信非但对孙应鳌个人的学术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就整个黔中王门学术的建构来说,更是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黔中王门的形成缘起于王阳明的龙场悟道。悟道后,王阳明创办龙岗书院“以讲学化夷”,居文明书院为诸生讲“知行合一”之旨,于是“黔人争知求心性”,而得阳明之传者首推陈文学(字宗鲁)和汤冔(字伯元)两人,“宗鲁得阳明之和,先生(伯元)得阳明之正,文章吏治,皆有可称”。陈文学、汤冔两人“承良知之派以开黔学”,首创之功不可磨灭,但黔中王门学术思想体系的建立则有赖于以马廷锡、李渭、孙应鳌等为代表的黔中王门第二代弟子的共同努力,正如谢圣纶在《滇黔志略》中所言:“李同野、孙淮海、马内江三先生皆崛起黔南,毅然以斯道为己任,青螺先生所谓‘可以无愧龙场’也。”这里“可以无愧龙场”即得王阳明之真传。马廷锡、李渭、孙应鳌三人学术虽有所不同,但均能“躬行实践,体道入微,卓然为后学典型”,故为学界所尊崇,“非但振拔超群,为全黔一时山斗也”。更难能可贵的的是,马廷锡、李渭、孙应鳌三人作为黔中本土学者,已经能与“并时诸子争雄长”,“孙文恭崛起起清平,李同野振拔于思南,马内江奋迹于宣慰,人文之盛,几与中华争烈”。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成就,才使得黔中王门在整个王门后学中占有一席之地,而这些皆与蒋信有着重要的关系。首先,蒋信任贵州提学副使长达四年之久,其在贵阳的讲学是继王阳明之后的最大规模的一次学术输入,尤为重要的是蒋信将湛若水的“随处体认天理”“圣学以求仁为要”等思想带入贵州,提倡“践履笃实,不事虚谈”的学风,这也使得黔中王门在学术建构开始时即对王学流弊有了清楚的认识,从而进一步涵养了黔中王门重视躬行实践的品性,也避免了滑向空疏、浅薄的流弊之中。其次,黔中王门第二代弟子的代表马廷锡、李渭、孙应鳌三人都与蒋信有着甚深的学术渊源。李渭少年时即随其父从学于蒋信,但执著于“自却妄念”“谨一介取与”之念,后蒋信“破其拘挛”,使其廊庑大开。作为入门弟子的马廷锡更是一路追随蒋信,在蒋信去世后,又远赴桃岗治丧,并请为蒋信立祠,“以无坠先生之教”。为弘扬蒋信之说,马廷锡在贵阳讲学三十余年而不辍,“听者常数百人”,这也形成继王阳明、蒋信之后的第三个讲学高峰,故莫友芝称赞说“盖自阳明、道林后仅见”。马廷锡曾于城南渔矶上构栖云亭,“南方学者争负笈请业,渔矶栖云间俨嗣桃岗之威”,显然,贵阳已经成为宣传蒋信之说的又一个中心。马廷锡讲学不倦,“兴起成就者甚众”,“兴起成就者”即是黔中王门的第三代弟子,由此亦可想见蒋信之说对贵州学术思想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如果说王阳明是黔中王学奠基者的话,那么蒋信则可以说是黔中王门学术思想建构的直接指导者。相较于其他王门后学而言,蒋信对黔中王门的影响无疑是巨大而且极其深远的,其在黔中王门学术思想体系的建构中占据着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考证,对于重新思考黔中王门学术思想的整体特色以及历史地位,均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为了适应阅读,略去注释和参考文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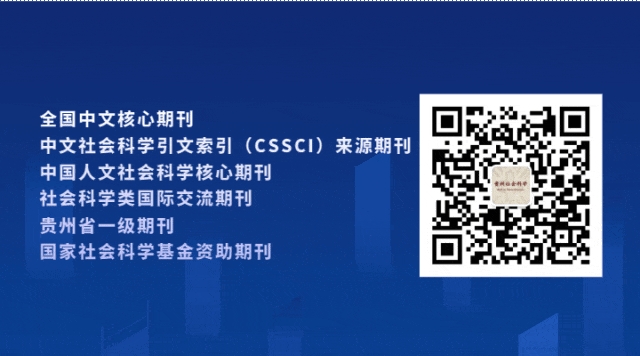
原载:《贵州社会科学》2024年第03期
转载来源:贵州社会科学 2024-05-30
一审:王凤梅 二审:何茂莉 三审:张清
编发:中国文化书院(阳明文化研究院)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 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