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文摘》2024年第20期“论点摘编”刊发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原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论文论点摘编。题:道家“垂钓”寓言的思想取向及论理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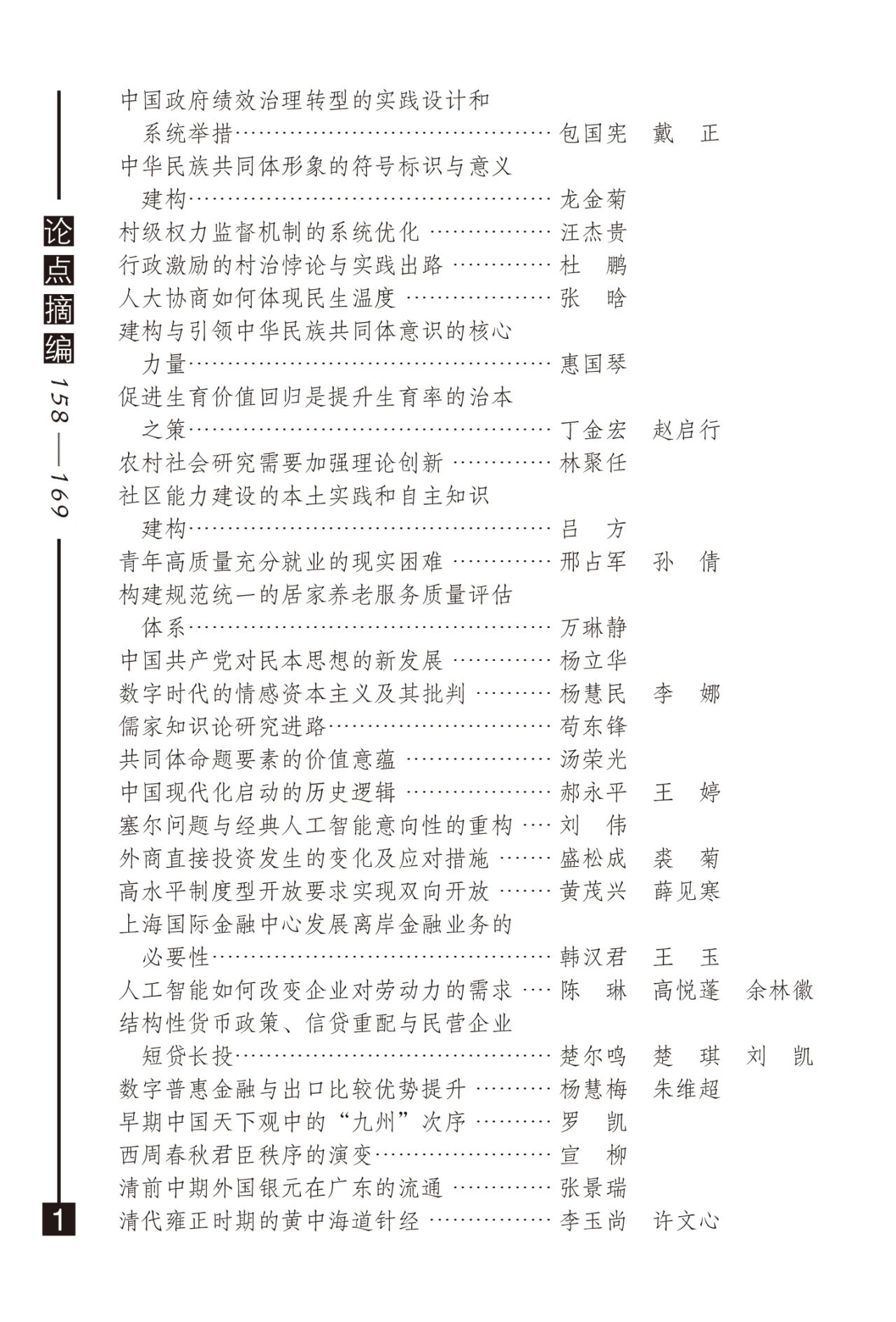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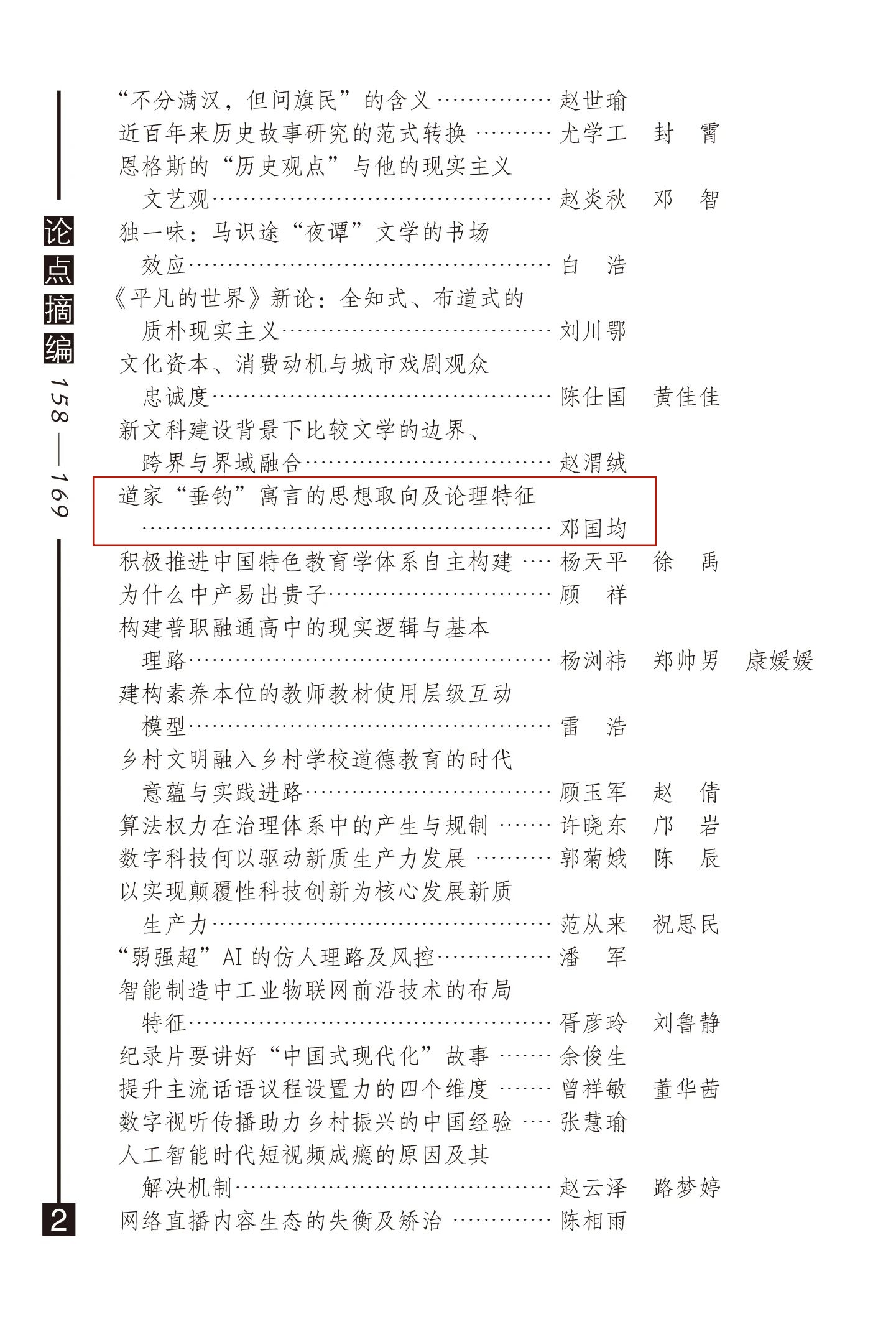

道家“垂钓”寓言的思想取向及论理特征
摘要:道家著作中的“垂钓”寓言具有丰富的哲学思想内涵。《庄子·秋水》篇所载“庄子之钓”,作为庄子“无为”“无待”的人生价值取向之象征,既是对《逍遥游》《齐物论》等篇哲学思想的生动演绎,亦是对庄子自由意志和独立精神的精彩展现。同书《外物》篇所载“任氏之钓”,则以“大鱼”拟喻经世的“大道”,表达了作者以道治天下的追求和兼济天下的政治理想,其中心意旨是通过“垂钓”过程,喻示为政之要在于持之以恒、久久为功,不可急功近利、盲目短视。《列子·汤问》篇所载“詹何之钓”,则以“钓术”喻示养心、全神之“道术”,展示行为主体如何通过内在精神的凝聚,达到形神合一、以心驭物的精神境界。三篇寓言的思想主旨虽然有所不同,但皆是作者志趣、心境和内在风神的生动写照。“垂钓”其实是一种特定的“体道”方式。就论述方式而言,《庄子》《列子》所载“垂钓”寓言,体现了道家诸子即事以论道、言近而旨远的论理特征。这些寓言生动地说明“道不远人”:“道”就在身边,就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对其进行思考和体会。
关键词:道家;垂钓;无待;经世;道术;体道
作者:邓国均,文学博士,哲学博士后,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
作为一种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垂钓”,一直与中国古代文学和哲学有着不解之缘。《周易·系辞下》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1]。由此可见,《周易·离卦》的意旨,或与上古先民的渔猎生活有关。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进步,“垂钓”逐渐从古人求取生存物资的经济活动中解脱出来,成为一种兼具休闲娱乐、修养身心、颐神益智的社会文化活动,由此也更为频繁地进入文士和哲人的创作视野,成为他们表达某种生活理念、文化意趣或思想认识的重要题材。
据《庄子》《列子》《淮南子》等书记载,战国时代的道家学者,多为“就薮泽”“处闲旷”的“江海之士”,因此他们大都具有“钓鱼闲处”的生活经验。不但庄子可能进行过“垂钓”活动,詹何、娟嬛等更是以“钓术”闻名于世。道家诸子著作中的某些“垂钓”寓言,正是以悠久的渔猎文化传统为基础,并结合其个人的现实生活经验,赋予“垂钓”活动以丰富的哲学思想内涵。今试对《庄子》《列子》等书所载“庄子之钓”“任氏之钓”和“詹何之钓”等寓言的哲学思想内涵进行解析,进而对道家诸子寓言的论理特征作一点初步的探讨。
一、庄子之钓:“无为”与“无待”
《庄子》书中有不少以“庄子”为主人公的故事,如《逍遥游》所载庄子与惠子关于“瓠瓜”与“大树”的对话,《德充符》所载庄、惠关于“有情无情”的辩论,《秋水》所载“庄子钓于濮水”“惠子相梁”及庄、惠之间的“鱼乐之辩”等。这些故事对于了解庄子生平及其思想性格等,皆有一定的哲学史意义。
由于《庄子》以“寓言”“重言”等为主要论说方式,因此书中所载上古至战国时代的历史人物颇多。黄方刚研究后发现,这些历史人物的相互关系,“时代上绝对可能与大概可能之问对或交涉凡七十九次”[2]。徐复观也分析说:“《庄子》书中虽多寓言,但除完全架空的人物以外,对历史人物相互关系的行辈则从无紊乱”[3]。孙以楷、甄长松将《庄子》所载历史人物与早期史籍的相关记载对比后指出:“《庄子》中所及历史人物(包括重言人物,也包括寓言人物)的相互关系,即人物的行辈、姓字、国籍、身份、行踪等形式方面的框廓,十之八九是可靠的”[4]。由此推测,《庄子》所载与庄子本人相关的寓言故事,也应当具有一定的现实基础。
不过,寓言作为一种叙事文体,其叙事模式与注重事件真实性的史传存在一定差异。《庄子》内、外、杂篇的不同作者,正是巧妙借助于寓言叙事的灵活性与自由度,出入于历史和文学之间,以表现其隐微而深刻的哲学思想。《秋水》篇所载“庄子钓于濮水”故事正是这样一篇寓言作品:
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塗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塗中。”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塗中。”[5](P603-604)
《淮南子·齐俗训》说:“惠子从车百乘以过孟诸。庄子见之,弃其余鱼”[6]。两相参证,可知庄子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可能从事过“垂钓”活动。但这则寓言的叙事重点,却不在“垂钓”活动的具体过程。作者实际上是将“垂钓”作为庄子与楚使对话的背景,通过有关南楚“神龟”的对话,进一步赋予“垂钓”活动以更为丰富而深刻的思想意义。
除《秋水》篇外,《庄子·列御寇》亦载:“或聘于庄子。庄子应其使曰:‘子见夫牺牛乎?衣以文绣,食以刍叔,及其牵而入于大庙,虽欲为孤犊,其可得乎!’”[5](P1062)由此可知,《秋水》篇所载楚使之聘,可能也是有一定事实依据的。在列国纷争、诸侯尚贤的战国时代,这是最平常不过的事。正因如此,司马迁所作《庄子传》才将两个故事合二为一,以表现庄子的人生价值取向:
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大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7](P2145)
虽然文章风格与《秋水》篇“庄子钓于濮水”略有差异,但是思想主旨却基本一致。《天下》篇评述庄子学说曰:“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其于本也,弘大而辟,深闳而肆,其于宗也,可谓稠适而上遂矣”[5](P1098-1099)。《庄子传》亦称庄子“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7](P2144)。《秋水》篇所载庄子“垂钓”故事,确实极为生动地体现了庄子“时恣纵而不傥”“洸洋自恣以适己”的思想性格特征。
“庄子钓于濮水”,看起来是一个平淡无奇的开端。作者正在讲述的,也是一件最平常不过的小事。在现实生活中,每一位垂钓者,自然都期望“得鱼”。庄子也不能例外,因为最低的物质生活标准是从事其他社会活动的前提条件。与“垂钓”的物质收获相比,十金、百金的财富,县令、郡守的职务,就是更多世人争相追逐的目标了。至于万乘之国的卿相之位,则更是梦寐以求而难以实现之事。然而,当楚王的使者来至濮水之滨,许以楚国卿相高位之际,庄子竟然“持竿不顾”!庄子之所以如此不屑一顾,是因为他认为担任楚国的卿相,譬如“死已三千岁”的南楚神龟,与其留骨而贵于庙堂之上,不若生而曳尾于泥涂之中。
如此将“仕”与“隐”视为悬若天壤的“死”“生”两途,“庄子钓于濮水”也就具有了超越功名、富贵、利禄等现实生活意义,其哲学思想内涵也进一步凸显出来:“庄子之钓”是以一种看似“有为”和“有待”的生活姿态,表达其“无为”和“无待”的人生价值取向,以及“全神”“养德”的精神追求。
此种“无为”“无待”的人生哲学,正是《庄子》哲学思想的核心内容。其内篇《逍遥游》云:“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5](P17)。这是庄子对于“无待”境界的形象描述。从“故曰”所引出的结语看,达至“无待”境界的关键,主要在于对“功名”的超脱。对于“至人”“神人”“圣人”三者的关系,唐人成玄英说:“至言其体,神言其用,圣言其名。故就体语至,就用语神,就名语圣,其实一也。诣于灵极,故谓之至;阴阳不测,故谓之神;正名百物,故谓之圣也。一人之上,其有此三,欲显功用名殊,故有三人之别。此三人者,则是前文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人也。欲结此人无待之德,彰其体用,乃言故曰耳”[5](P22)。可见其涵义是具有一致性的。就表达方式来说,作者在这里似乎采用了“互文”的手法,如置以平常的叙述,则应是“至人、神人、圣人,无己、无功、无名”。“无己”“无功”和“无名”,皆是“无为”“无待”的人生哲学的具体体现,“无己”是“无功”“无名”的前提。
庄子之所以要绝弃功名、富贵、利禄等,是因为他认为追逐这些外在的目标只会给人带来精神的消耗,使人终生困苦而不得解脱。《齐物论》说:“一受其成形,不忘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薾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谓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5](P56)不仅功名为人生之累,对于知识的追逐,亦同样可能使人陷入迷途。《养生主》云:“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5](P115)。根据这些论述,我们对“庄子之钓”的思想内涵也可以有进一步的理解:从“心”与“物”的关系来说,庄子“垂钓”寓言中的“鱼”,在一定程度上象征着庄子的本心。庄子“持竿不顾”,不以卿相之位易三尺之竿,也即不以“外物”易其内在的本心。
如果说《秋水》篇所载庄子“垂钓”寓言,是从正面展示庄子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同篇所载“惠子相梁”故事,则又从侧面对此进行了印证。据《庄子·逍遥游》《德充符》《徐无鬼》等篇记载,惠子虽是庄子的至交好友,但两人的处世态度、价值观念、哲学思想等皆存在较大差异。庄子不尚功名富贵,而惠子却颇为热心仕进,曾长期担任梁国的相国之职。故事正是以此为切入点:
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代子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庄子往见之,曰:“南方有鸟,其名曰鹓雏,子知之乎?夫鹓雏,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鹓雏过之,仰而视之曰‘吓!’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吓我邪?”[5](P605)
故事一波三折,将庄子和惠子的处世态度、价值观念之差异,形象地转化为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又以庄子的主动出现,轻轻化解两者的冲突。全文通过庄子与惠子、鹓雏与鸱鸮的对比,生动地刻画出惠子汲汲于权势、利禄的渺小形象,衬托出庄子对功名、权位的淡漠态度和“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的高洁人格形象。无论是故事的思想主旨还是表现手法,皆与“垂钓”寓言有异曲同工之妙。
对于“垂钓”活动的文化功能和精神价值,庄子后学亦有相当深入的体会。《刻意》篇云:“语大功,立大名,礼君臣,正上下,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强国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薮泽,处闲旷,钓鱼闲处,无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闲暇者之所好也。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已矣;此道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5](P535)。由此可知,“钓鱼闲处”,正是主张“无为”的“江海之士”的典型生活方式。同篇又云:“若夫不刻意而高,无仁义而修,无功名而治,无江海而闲,不道引而寿,无不忘也,无不有也,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此天地之道,圣人之德也。故曰,夫恬惔寂漠虚无无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质也。故曰,圣人休休焉则平易矣,平易则恬惔矣。平易恬惔,则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故其德全而神不亏”[5](P537-538)。“无江海而闲,不道引而寿”,固然是达至“淡然无极”之境界的理想途径,但“就薮泽,处闲旷,钓鱼闲处”,亦未尝不是获得“平易恬惔”之心绪的有效方式。
从这些方面看,《秋水》篇所载“庄子之钓”,不但是对《逍遥游》《齐物论》等篇哲学思想的生动演绎,亦是庄子人生哲学与精神境界的精彩呈现,是他的内在精神、风骨与气象的真实写照。在纵横游说之风大行于世的战国时代,在天下学士辐辏于齐国稷下之际,庄子却坚拒楚王之聘而甘愿曳尾于“泥涂”之中,充分展现了他的自由意志和独立精神。《秋水》篇虽非庄子所作,但学者认为此篇当是“庄子弟子或其后学的作品”[8](P294)。故其文学与思想,皆可谓深得庄学之风神。
二、任氏之钓:“大道”与“经世”
《庄子》内、外、杂篇,其作者并非同一个人,亦非写作于同一时期。学者大都认为,《庄子》内七篇,应是庄子本人所作。外、杂篇则多出于庄子弟子及其后学之手。《秋水》篇为庄子弟子所作,故其思想与《逍遥游》《齐物论》等篇相通。杂篇的《则阳》《外物》等,与《庄子》内篇思想则有所不同。
《外物》篇旧本分为十余章,首尾皆为议论,中间则依次载述“庄周贷粟于监河侯”“任公子钓于东海”“儒以《诗》《礼》发冢”“老莱子弟子遇仲尼”“宋元君梦神龟”“惠子谓庄子”等故事。其中任公子“垂钓”故事,因文中包含“小说”一词,历来为研究中国小说史者所重视。其文云:
任公子为大钩巨缁,五十犗以为饵,蹲乎会稽,投竿东海,旦旦而钓,期年不得鱼。已而大鱼食之,牵巨钩,錎没而下,鹜扬而奋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荡,声侔鬼神,惮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鱼,离而腊之,自制河以东,苍梧已北,莫不厌若鱼者。已而后世辁才讽说之徒,皆惊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灌渎,守鲵鲋,其于得大鱼难矣。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是以未尝闻任氏之风俗,其不可与经于世亦远矣。[5](P925)
成玄英解释“辁才讽说”句曰:“末代季叶,才智轻浮,讽诵词说,不敦玄道,闻得大鱼,惊而相语。轻字有作辁字者,辁,量也”[5](P926)。从下文看,“辁才讽说之徒”即那些“饰小说以干县令”者。在作者看来,他们的行为与言说,犹如那些“揭竿累,趣灌渎”的钓者,是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大鱼”的。
对于“饰小说以干县令”,成玄英说:“干,求也。县,高也。夫修饰小行,矜持言说,以求高名令闻者,必不能大通于至道。字作县者,古悬字多不著心”[5](P927)。如此将“小说”分为“修饰小行”和“矜持言说”两个方面,又以“县”为“悬”之假借,将“县令”解作“高名令闻”,其实皆不是很确切。宋人马永卿说:
仆以上下文考之,“揭竿累以守鲵鲋,其于得大鱼亦难矣;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盖“揭竿累”以譬“饰小说”也,“守鲵鲋”以譬“干县令”也。彼成玄英肤浅,不知庄子之时已有县令,故为是说。《史记·庄子传》:庄子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史记·年表》:“秦孝公十二年,并诸小乡聚为大县,县一令。”是年乃梁惠王之二十二年也。且周尝往来于楚、魏之间,所谓监河侯,乃西河上一县令也。[9]
清人刘凤苞亦认为:“县令”不当作“高名令闻”解,“作县令解,方与趋灌渎之喻相符”[10]。马叙伦进一步指出:“县读为‘郡县’之‘县’。《史记·赵世家》:‘以万户都三封太守,千户都三封县令。’是战国时县小于郡,县长称令矣”[11]。可见,这里所谓的“饰小说”,实际上就是对“县令”的一种游说活动。
由于对“小说”“县令”等词的理解不同,学者对于此篇写作时代的看法也存在一些分歧。罗根泽说:“小说之名,不见于先秦载籍;‘县令’,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上》,是秦官,而汉代承用之”,由此他认为《外物》篇应是“西汉作品”[8](P305)。张恒寿则认为,“《外物》篇首章,是取自《吕氏春秋·必己》篇,大约成于刘安门客之手”,其余“庄周贷粟于监河侯”“任公子钓于东海”“老莱子弟子遇仲尼”等故事,则应是先秦时期的作品。他还具体解析了“任公子钓于东海”故事,“它用‘饰小说以干县令’作为比喻,仍是战国末秦国未统一以前的习惯用语,及至秦、汉以后,采用游说以干人主之事已成过去,似已不成为随手拈来作为一般批评的对象了”,他由此认为,“此章当作于《韩非子》、《吕氏春秋》时代。马永卿认为系庄周时作,罗根泽氏说是秦汉时作,似俱不符事实”[12](P277)。张氏对于此章写作年代的考辨,应该是大致可信的。
庄子后学中的部分人,对政治表现出比庄子更大的热情。这在《庄子》外篇之《天地》《天道》《天运》等篇有颇为明显的体现。这几篇皆以治国理政作为思想主题,以圣人之治、帝王之德作为最高理想。《天地》篇云:“天地虽大,其化均也;万物虽多,其治一也;人卒虽众,其主君也。君原于德而成于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无为也,天德而已矣。以道观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观分而君臣之义明,以道观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泛观而万物之应备”[5](P403-404)。此即以“道”治天下之义。此篇又解释“圣治”的涵义说:“官施而不失其宜,拔举而不失其能,毕见其情事而行其所为,行言自为而天下化,手挠顾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谓圣治”[5](P440)。《天道》篇亦解释“帝王之德”的内涵说:“天道运而无所积,故万物成;帝道运而无所积,故天下归;圣道运而无所积,故海内服。明于天,通于圣,六通四辟于帝王之德者,其自为也,昧然无不静者矣”;“夫帝王之德,以天地为宗,以道德为主,以无为为常。无为也,则用天下而有余;有为也,则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贵夫无为也”[5](P457-465)。据此可知,作者实际上是以“无为”作为“圣人之治”“帝王之道”的根本原则,“无为”的目标实际上还是“有为”。
这几篇的思想主旨,与庄子对于政治的认识和态度,确实存在一定的差异,但与《外物》等篇在思想上则有某些相合之处。张恒寿分析任公子“垂钓”故事说:“‘其不可与经于世亦远矣’,说明作者之理想在于‘大达’‘经世’,和《逍遥游》、《秋水》、《则阳》等篇中所追求的超世理想截然殊科。《外物》此章所说的‘大’,正是《逍遥游》等篇所说的‘小’”[12](P277)。不过,庄子本人虽然不愿意入仕,但对于政治并非漠不关心。《逍遥游》所载姑射山神话,借助“连叔”之口评论姑射山“神人”说:“之人也,之德也,将旁礴万物以为一,世蕲乎乱,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之人也,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是其尘垢秕糠,将犹陶铸尧舜者也,孰肯以物为事!”[5](P30-31)此章所透露的庄子的政治意识和态度,其实是相当微妙的。不愿、不肯“以天下为事”,只是一种主观态度上的拒斥,与客观上的“不能”迥然有别。
《天下》篇称庄子“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故其著书多采用“寓言”“重言”“卮言”为主的“三言”模式,对现实政治表现出相对疏离的态度。但如果我们仔细考察,又可以发现内篇的《逍遥游》《大宗师》《应帝王》等,亦不时可见有关“君天下”“治天下”“为天下”的讨论。《应帝王》篇载狂接舆之言云:“夫圣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后行,确乎能其事者而已矣。”同篇又载:“无名人曰:‘汝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又载老聃之言云:“明王之治: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贷万物而民弗恃;有莫举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测,而游于无有者也”[5](P291,294,296)。在以“庄语”形式写成的《天下》篇中,庄子又以“古之道术”和“内圣外王之道”作为评论百家学说的标准{1}。因此,《天地》《天道》《天运》等篇的政治思想,亦可视作是由庄子思想发展演变而来,只不过其中增加了一些儒家思想的成分而已。
《外物》篇所载任公子“垂钓”故事,所包含的政治思想与《天地》《天道》等篇十分相近。“任公子为大钩巨缁,五十犗以为饵,蹲乎会稽,投竿东海,旦旦而钓,期年不得鱼”,这样宏大的场景,非凡的气象,充分体现了作者卓越的想象力,与《逍遥游》开篇的鲲鹏寓言有异曲同工之妙。从下文内容看,其实任公子并非“不得鱼”,而是不得“大鱼”。任公子“旦旦而钓,期年不得鱼”,看似是一个客观上的无奈结果,实则是其主观上的“无为”思想之反映。“不得鱼”是为了“得大鱼”,“无为”是为了进一步的“有为”。因此,当“已而大鱼食之”,任公子即“离而腊之,自制河以东,苍梧已北,莫不厌若鱼者”。这就是下文所云“任氏之风俗”,也即任氏的“经世之道”。作者将“任氏之钓”与“揭竿累,趣灌渎,守鲵鲋”的垂钓者相对比,指出“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表明“小说”实乃“小道”的体现,而“大鱼”则是“大道”的象征。“任氏之钓”体现了以道治天下的追求和兼济天下的政治理想,其核心意旨是通过“垂钓”的过程,喻示为政之要在于持之以恒、久久为功,不可急功近利、盲目短视。
任公子垂钓之地,位于“会稽”和“东海”。就其地域文化背景而言,此篇寓言似与《列子》《山海经》所载上古神话有一定关联。《列子·汤问》云:“渤海之东不知几亿万里,有大壑焉,实惟无底之谷,其下无底,名曰归墟。八纮九野之水,天汉之流,莫不注之,而无增无减焉。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舆,二曰员峤,三曰方壶,四曰瀛洲,五曰蓬莱”,“五山之根无所连箸,常随潮波上下往还,不得暂峙焉。仙圣毒之,诉之于帝。帝恐流于西极,失群仙圣之居,乃命禺强使巨鳌十五举首而戴之。迭为三番,六万岁一交焉。五山始峙而不动。而龙伯之国有大人,举足不盈数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钓而连六鳌,合负而趣,归其国,灼其骨以数焉。员峤二山流于北极,沈于大海,仙圣之播迁者巨亿计”[13](P151-154)。“一钓而连六鳌”的龙伯国“大人”,与“投蹲乎会稽,投竿东海”的“任公子”,确实有某些相似之处。《山海经·大荒东经》亦载:“东海之外(有)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弃其琴瑟”;“东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言,日月所出。有波谷山者,有大人之国”[14]。据此则“东海之外”的“大壑”与“大荒”,乃是“少昊之国”与“大人之国”的所在地。《左传·僖公二十一年》云:“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大皞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15]。如此则“任”“宿”等氏,皆为“风姓”,乃“太皞”的后裔。相互比较,可知“投竿东海”而钓得“大鱼”的“任公子”,实由《山海经》《列子》等书所载上古神话中的“大人”演变而来,故其活动地域亦与“任氏”世居之地,以及东部滨海地区的“大人之国”接近。由此可见,“任氏之钓”虽属哲理寓言,但作为故事主人公的“任公子”,亦并非信手拈来的“子虚乌有”先生,而有一定的历史文化依据。
《庄子·外物》篇的作者,巧妙地从古代神话取材,以创作道家化的哲理寓言,表达其以“道”治天下的追求和兼济天下的政治理想。《秋水》篇所载“庄子之钓”和《外物》篇所载“任氏之钓”,皆与道家的“无为”思想相关。前者以“无为”为指归,后者则以“无为”为前提,而以“有为”为宗旨。两篇寓言的思想主旨虽然有所不同,但又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早期道家思想的发展和演变。
三、詹何之钓:“形神”与“道术”
《秋水》篇所载“庄子之钓”,突出了“垂钓”所具象征意义;《外物》篇所载“任氏之钓”,则侧重“垂钓”结果所隐喻的思想内涵,但就故事情节而言,两篇寓言都不以“垂钓”活动过程作为叙述重点。《列子·汤问》篇所载“詹何之钓”,则将詹何“钓术”作为叙事重心,通过对詹何“垂钓”活动过程的详细描述,抉发出道家“垂钓”寓言的另一层思想涵蕴。
詹何、娟嬛皆为战国时代的道家学者,二人皆为隐居的避世之士,又同以“善钓”著名于世。在《庄子》书中,詹何又被写作“瞻子”。《庄子·让王》篇:“中山公子牟谓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则利轻。’中山公子牟曰:‘虽知之,未能自胜也。’瞻子曰:‘不能自胜则从,神无恶乎?不能自胜而强不从者,此之谓重伤。重伤之人,无寿类矣。’”[5](P979-980)唐人陆德明《经典释文》云:“‘瞻子’,贤人也。《淮南》作‘詹’”[16]。《吕氏春秋·执一》篇亦载:“楚王问为国于詹子,詹子对曰:‘何闻为身,不闻为国。’”高诱注云:“詹何,隐者”[17](P469)。同书《审为》篇:“中山公子牟谓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奈何?’”汉末高诱注云:“詹子,古得道者也”[17](P592)。由于詹何以“善钓”著名,故而“中山公子牟”的发问,即从“身在江海之上”入手。《淮南子·道应训》所载公子牟与詹何的对话,内容与《吕氏春秋·审为》篇《庄子·让王》篇基本相同,三者应有相同的来源[6](P390)。由此亦可证《庄子·让王》篇所云“瞻子”,确为《吕氏春秋·审为》《淮南子·道应训》等篇所载詹何。
由于詹何、娟嬛皆以“善钓”著名,故而《列子》《淮南子》等道家著作,即以二人作为“钓者”的代表。《淮南子·原道训》:“夫临江而钓,旷日而不能盈罗,虽有钩箴芒距、微纶芳饵,加之以詹何、娟嬛之数,犹不能与网罟争得也”[6](P11-12)。同书《说山训》:“詹公之钓,千岁之鲤不能避”。由此可见,詹何“善钓”的故事,在西汉时代仍有广泛的流传。《列子·汤问》篇正是以相关传说为基础,赋予“垂钓”活动以新的思想意义:
均,天下之至理也,连于形物亦然。均发均县,轻重而发绝,发不均也。均也,其绝也莫绝。人以为不然,自有知其然者也。詹何以独茧丝为纶,芒针为钩,荆篠为竿,剖粒为饵,引盈车之鱼于百仞之渊、汩流之中;纶不绝,钩不伸,竿不挠。楚王闻而异之,召问其故。詹何曰:“臣闻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纤缴,乘风振之,连双鸧于青云之际。用心专,动手均也。臣因其事,放而学钓。五年始尽其道。当臣之临河持竿,心无杂虑,唯鱼之念;投纶沉钩,手无轻重,物莫能乱。鱼见臣之钩饵,犹沉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强,以轻致重也。大王治国诚能若此,则天下可运于一握,将亦奚事哉?”楚王曰:“善。”[13](P171-173)
晋人张湛注云:“詹何,楚人,以善钓闻于国”[13](P172)。《淮南子·览冥训》:“精神形于内,而外谕哀于人心,此不传之道。使俗人不得其君形者而效其容,必为人笑。故蒲且子之连鸟于百仞之上,而詹何之骛鱼于大渊之中,此皆得清净之道,太浩之和也。”高诱注说:“詹何,楚人知道术者也。言其善钓,令鱼驰骛来趋钩饵,故曰骛鱼”[6](P194)。詹何对于“钓术”的阐述,与《览冥训》有关“精神”的论述是高度相通的。
《列子·汤问》篇虽然将“詹何之钓”与“均”理相关联,但从詹何对于“钓术”的解说看,这个故事的思想主旨,实是借“钓术”喻示形、神合一的“道术”。可能是本篇作者将取自他书的成文予以改编,以阐释其所理解的“均”这一“至理”。从故事内容看,詹何“钓术”的关键,主要在于“用心专”,也即所谓“心无杂虑,唯鱼之念”。由“用心专”而达到内在精神的高度凝聚,故而在“投纶沉钩”的过程中,才能做到“手无轻重,物莫能乱”。垂钓过程中的“动手均”,乃是精神专一的一种表现形式。所谓“用心专,动手均”,实即形神合一、以心驭物,从而取得“以弱制强,以轻致重”的效果。因此,此种“钓术”,实为一种养心、全神之“道术”。人和鱼的关系,乃是“心”与“物”关系之象征。
《汤问》篇所载“詹何之钓”的思想主旨,与《庄子》书中的某些寓言相通。《庄子·逍遥游》描述“神人”的精神特征说:“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5](P28)。庄子以精神的内聚作为全德、养生的根本,故《德充符》载其批评惠子学说云:“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无以好恶内伤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劳乎子之精,倚树而吟,据槁梧而瞑。天选子之形,子以坚白鸣!”[5](P222)《庄子》外、杂篇中的某些寓言,即是对庄子“形神”思想的演绎。如《达生》篇:
仲尼适楚,出于林中,见痀偻者承蜩,犹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坠,则失者锱铢;累三而不坠,则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坠,犹掇之也。吾处身也,若厥株拘;吾执臂也,若槁木之枝;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侧,不以万物易蜩之翼,何为而不得!”孔子顾谓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其痀偻丈人之谓乎!”[5](P639-641)
痀偻丈人“承蜩”,之所以能够达到犹如“掇之”的效果,关键在于“用志不分”。此与“詹何之钓”的“用心专”,实出于同样的原理。丈人在“承蜩”之时,“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不以万物易蜩之翼”;詹何在“垂钓”过程中,亦“心无杂虑,唯鱼之念”,“手无轻重,物莫能乱”,故而皆能实现内在精神的高度凝聚,达到形神合一、以心驭物的精神境界。同篇又载:
纪渻子为王养斗鸡。十日而问:“鸡已乎?”曰:“未也,方虚 而恃气。”十日又问,曰:“未也,犹应向景。”十日又问,曰:“未也。犹疾视而盛气。”十日又问,曰:“几矣。鸡虽有鸣者,已无变矣,望之似木鸡矣,其德全矣,异鸡无敢应者,反走矣。”[5](P654-655)
纪渻子所养斗鸡,经历了“虚而恃气”“犹应向景”“疾视而盛气”等几个阶段,但此种精神状态的斗鸡,皆非真正的善斗者,唯有“望之似木鸡”者,方能取得“异鸡无敢应”的无敌效果。故事以“十日”为时间线索,清晰地反映了此种精神变化的过程。“望之似木鸡”者之所以能无敌,主要在于其已达到“其德全矣”的精神境界。其根本即在于内在精神的高度凝聚,所谓“德全”也即“神全”。此与詹何“垂钓”过程中的“心无杂虑”“物莫能乱”亦高度相通。
《汤问》篇所载“詹何之钓”,虽以“用心”“凝神”作为詹何“钓术”的关键,但此则寓言的思想旨趣还不限于此。詹何于叙述“钓术”之后话锋一转,向楚王指出:“大王治国诚能若此,则天下可运于一握。”可见这则寓言的作者是以詹何独特的“钓术”喻示“以弱制强,以轻致重”的“治术”。这与詹何的“重生”思想,亦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庄子·让王》篇、《吕氏春秋·审为》篇以及《淮南子·道应训》所载詹何与中山公子牟的对话,皆强调“重生”的意义,并以之作为“治国”的根本。《列子·说符》篇亦载:
楚庄王问詹何曰:“治国奈何?”詹何对曰:“臣明于治身而不明于治国也。”楚庄王曰:“寡人得奉宗庙社稷,愿学所以守之。”詹何对曰:“臣未尝闻身治而国乱者也,又未尝闻身乱而国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对以末。”楚王曰:“善。”[13](P258)
《淮南子·道应训》所载“楚庄王问詹何”,对话内容与此相同[6](P390)。高华平认为,詹何“将老子的圣人‘长生久视’之说,发展为一种尊生贵己、养性全生之论”,又把“‘重生’和‘养生’学说与‘治国’‘为国’的‘外王’之道结合起来,由‘为身’而推及‘为国’”[18]。《汤问》篇所载“詹何之钓”,确实清晰地反映了詹何由“治身”而推及“治国”的思想特点。有学者研究认为,《庄子·外物》篇的“任公子”,即《列子·汤问》所载楚人詹何[19]。虽然两则寓言的思想主旨皆与“治术”相关,但其侧重点明显不同。詹何为历史上的真实人物,“任公子”则含有虚构成分,两者应该不是同一个人。
《庄子·在宥》篇通过黄帝和广成子的对话,论述了“养生”之道的根本原则:“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心静必清,无劳女形,无摇女精,乃可以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女神将守形,形乃长生”[5](P381)。“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固然是养生、全神的理想模式,但人既然生活在社会关系中,难免要与外部世界相接触。《庄子·达生》篇所载“痀偻丈人承蜩”和“纪渻子养斗鸡”,以及《列子·汤问》篇所载“詹何之钓”等寓言,则从各不相同的角度,喻示了人在社会生活中如何由“术”而体“道”,可谓是对庄子养生、全神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四、余 论
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中,道家擅长以寓言的形式讲述抽象哲理。《庄子·寓言》篇说:“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论之”[5](P947-948)。同书《天下》篇亦云:“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5](P1098)。这些有关“寓言”的论述,具有一定的“自叙体例”性质,体现了庄子及其后学对寓言文体功能的认识。
所谓“寓言十九,藉外论之”,郭象注说:“寄之他人,则十言而九见信。”成玄英进一步解释说:“寓,寄也。世人愚迷,妄为猜忌,闻道己说,则起嫌疑,寄之他人,则十言而信九矣。故鸿蒙、云将、肩吾、连叔之类,皆寓言耳”[5](P947)。据此则郭象和成氏皆以“寓”为“寄寓”“寄托”之意,“寓言”,即将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寄寓”于他人的言行,因此也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代言”。这种借助于他者的“代言”形式,比起主观化的自我陈述更能取信于人,因此“寓言”具有更好的推广、拓展作用。这应当是道家诸子大量创作寓言的重要原因。
《庄子》《列子》所载“垂钓”寓言,皆是道家哲理寓言的突出代表。这些寓言虽然皆取材于日常生活,但所表达的思想主题却各不相同。《秋水》篇所载“庄子之钓”,是庄周“无为”“无待”思想之体现。《外物》篇所载“任氏之钓”,则是以“大鱼”拟喻经世之志,喻示为政之要在于持之以恒、久久为功。《列子·汤问》篇所载“詹何之钓”,实以“钓术”喻示养心、养神之“道术”,展示行为主体如何通过内在精神的凝聚,达到形神合一、以心驭物的精神境界。道家“垂钓”寓言对相同题材的多角度呈现和不同思想主题的演绎,既是中国特色哲学话语方式的生动展现,亦体现了道家诸子寓言所取得的艺术成就。
道家“垂钓”寓言的思想主旨虽然有所不同,但“垂钓”活动又皆是其作者志趣、心境和内在风神的生动写照,“垂钓”实为一种特定的“体道”方式。除此以外,《庄子·养生主》所载“庖丁解牛”,《天道》篇所载“轮扁斫轮”,以及《列子·汤问》篇所载“师文鼓琴”等寓言,其取材范围和论理方式,皆与“垂钓”寓言有相似之处。这些寓言故事,皆与现实生活中的某种“术”相关。故事中的人物,大多因“物”以言“心”,由“术”而体“道”,即形而下之器,以达形而上之思。因此也可以说,道家诸子著作中的这类寓言,鲜明地体现了即事以论道、言近而旨远的说理特征。其作者通过这些寓言,生动地说明“道不远人”:“道”就在身边,就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对其进行思考和体会。
注:
{1} 从文体形式看,《天下》篇为《庄子》全书的序言。学者或疑其非庄子本人所作,但所举证据大都难以成立。故我们持比较传统的看法,认为《天下》篇应是庄子之作。
【参考文献】
[1] (唐)孔颖达.周易正义[A].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86.
[2] 黄方刚.老子年代之考证[A].古史辨(第四册)[M].上海:上海书店,1992.376.
[3] 徐复观.有关老子其人其书的再检讨[A].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篇[M].上海:上海书店,2004.175.
[4] 孙以楷,甄长松.庄子通论[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27.
[5] (清)郭庆藩.庄子集释[M].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61.
[6] 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9.373.
[7] (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8] 罗根泽.庄子外杂篇探源[A].诸子考索[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9] (宋)马永卿.嬾真子[M].北京:中华书局,1985.28.
[10] (清)刘凤苞.南华雪心编[M].北京:中华书局,2010.697.
[11] 马叙伦.庄子义证[M].李林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9.596.
[12] 张恒寿.庄子新探[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
[13] 杨伯峻.列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79.
[14] 山海经校注[M].袁珂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1980. 338+340-341.
[15]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0.391-392.
[16] (唐)陆德明.经典释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399.
[17] 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9.
[18] 高华平.先秦诸子与楚国诸子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109-110.
[19]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238.
论文原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
论点摘编信息来源:“新华文摘杂志”公众号 2024年10月28日
一审:王凤梅 二审:何茂莉 三审:张清
编发:中国文化书院(阳明文化研究院)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 办公室